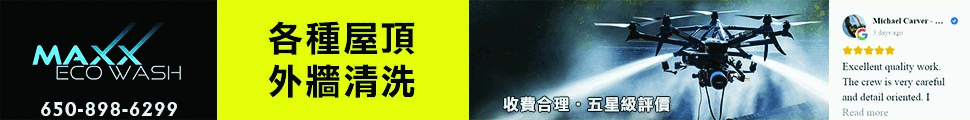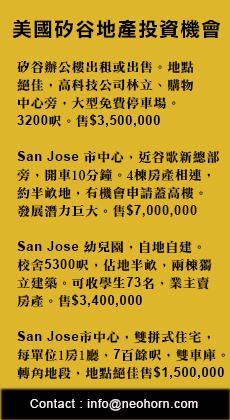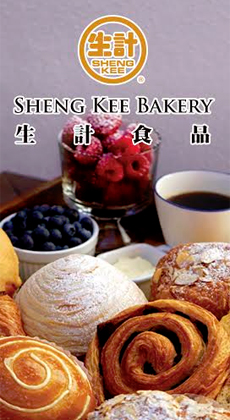11月份,我辭去了《連線》(Wired)雜誌主編的工作,開始經營3D機械人技術公司(3D Robotics)。3年前,作為一項副業,我與一名合作夥伴一起開辦了這家位於聖地亞哥的無人機公司。我們研製自動駕駛技術和能夠自己飛行的小型飛機,包括飛機和多旋翼直升機。這些無人機為民用,每個售價幾百美元,它們沒有射擊功能,可拍照和攝像。它們的製作過程非常有意思(我們藉助了機械人的大量幫助)。為了這一行而放棄出版業不是一個太難的決定。
但就像許多製造商一樣,我的公司也面臨著一個相似的挑戰:它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公司,它們具有廉價勞力和一流工藝兩方面的優勢。所以,當我們去年進行一輪融資時,風險投資家們很自然地提出,他們需要我們給出一個合理解釋,我們這家新創立的小公司如何可以戰勝中國對手。這個問題的答案出乎投資者的意料,幾年前也曾讓我感到意外:墨西哥。準確地說是蒂華納(Tijuana,簡稱TJ)。
就像許多美國人一樣,直到最近,當我聽到“蒂華納”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只能想到販毒集團和廉價龍舌蘭酒。其實,“TJ”是一個擁有兩百多萬人口的城市(比相鄰的聖地亞哥要多),已經成為北美洲電子產品裝配的熱點城市。大多數由三星(Samsung)和索尼(Sony)等公司出品、在美國出售的平面電視都是在這裡製造的,這裡還生產從醫療器械到航空設備部件等各種產品。霍爾迪·穆尼奧斯(Jordi Muñoz)這個聰明的年輕人教了我關於無人機的知識,隨後和我一起開辦了3D機械人技術公司,他來自TJ,並說服我在那裡開辦了第二座工廠,來補充我們在聖地亞哥的生產。
我們穿梭於這兩座工廠之間,在聖地亞哥設計、製造我們的無人機,並在TJ進行組裝,這讓我回憶起10年前的一次類似的經歷。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我住在香港(為《經濟學人》雜誌工作),目睹這個城市如何與邊界那邊中國內地廣東深圳的“經濟特區”配對。這兩座城市一起打造了一座世界領先的製造業中心:在香港完成商務、設計和財務工作,在深圳進行製造。這兩座城市的明確分工,成為了當代中國的典範。
今天,蒂華納之於聖地亞哥就如同深圳之於香港。從我們聖地亞哥的工程中心出發,駕車20分鐘就可以到達蒂華納的工廠,不需要護照。(想要返回需要護照,但有針對商務人士的快速通道。)我們的一些僱員每天上下班都穿越邊境。在TJ好醫生比較便宜,也較易找到,私立學校也是一樣,不過聖地亞哥的生活總體上還是更好些。從某些方面來說,這條邊境線感覺更像是歐盟各國名義上的邊界線,而不是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隔開的界限。
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TJ。在它東部的華雷斯,生產世界上超過40%電子產品(包括蘋果的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正在生產戴爾電腦。在它南部的克雷塔羅,一家工廠正在生產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安裝在克爾維特(Corvette)跑車上的變速器。通用電氣的GEnx渦輪噴氣發動機的設計和波音787夢想客機內部組件的製造也是在墨西哥完成的。製成品是該國的主要出口商品,該國製造業的私營投資也屬於世界最高水平。
認為墨西哥僅僅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想法完全是不着邊際的。墨西哥每年有11.5萬名工程類學生畢業,在人均水平上大約是美國的三倍。其結果之一便是,想在TJ找一些機械類專家比在許多美國大城市要更容易。就這一點而言,在生產經濟學上有經驗的會計師和其他高技術工人也在墨西哥比較多。
所有這些結合便形成了這樣一種模式。美國製造商如何與來自中國、印度以及下一代經濟強國的製造商競爭,這種模式或許就是我們長久以來尋找的答案。因為TJ模式和外包沒有太多關係,而是“快包”。這種方法也可以在美國創造成千上萬的好工作。
任何企業家都會告訴你,供應鏈越短越好、越靈活越好。
首先,一條較短的供應鏈意味着,一家公司可以在想要生產的時候生產,而不僅僅是在它必須生產時生產。這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但許多小型生產商沒有這種選擇。當我們創建3D公司時,我們在中國生產每一件東西,一次就要訂幾千件,才能拿到一個好價格。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寫下大額支票,來購買大批商品,在我們賣出所有那些產品之前,收不回這筆錢,這有時需要一年或更久。現在我們在本地進行生產,我們就能夠僅僅生產我們這一周所需的。
第二,這樣做風險更小。假如我們在設計中出了一個錯,我們已經浪費的生產時間最多幾天。假如我們的生產過程本身出了什麼問題,我們能很快發現。我們控制着部件的清單,因此我們很清楚,裝入我們產品的是什麼,也知道我們不會多花錢買進二手或盜版部件。而且如果我們想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我們可以做到,無須依靠其他公司將我們的利益置於首位。這還沒有考慮任何政治、環境或公關風險。像蘋果和沃爾瑪這樣的公司已經在中國通過教訓認識了這些風險。
第三,速度絕對會更快。我們仍舊從中國訂購一些部件,即便使用聯邦快遞,都似乎總要花上數周,乃至數月,這總比我們計劃的要長。這並非是在批評中國,對於所有關係較遠的小買家和大製造商來說,這就是它們關係的本質。假如我們是蘋果,我們可能能得到連夜生產的服務。但我們不是,所以我們就只好等。
最後一點是,一條短的供應鏈可以激勵創新。假如你把一件產品的大量生產外包,你就無法對這件產品進行改動,直到你把已生產的所有商品賣光為止(如果你想繼續留在這個行業,你就不能進行改動)。因此這通常意味着這些產品會留在你手上,得等到第一版賣光了才能開始製造第二版。但在你進行適時生產時,如果想要,你可以每天做改動,不論是使用一些更好的、更便宜的部件,還是改進設計。
同時,在長供應鏈的領域,事情也在變化。在中國,通脹調整後的勞動力成本,在過去十年已經漲到原來的三倍還多。中國南部城市的工資水平正在接近每小時6美元(約合37元人民幣),這和墨西哥的工資水平差不多。
不過這些因素是否足以把美國企業從“外包者”變為“快包者”,這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我拿自己的錢下注,它們會。1997年我從香港前往深圳時,我所感覺到的可能性,和我現在從聖地亞哥去蒂華納時的感覺是一樣的。21世紀的貿易路線,並不一定非要沿着馬可·波羅(Marco Polo)從西到東的方向。在新的製造業領域,這些路線完全不用太長。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是美國《連線》雜誌前主編,以及《製造商:新工業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書的作者。
文章出處:紐約時報
翻譯:林蒙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