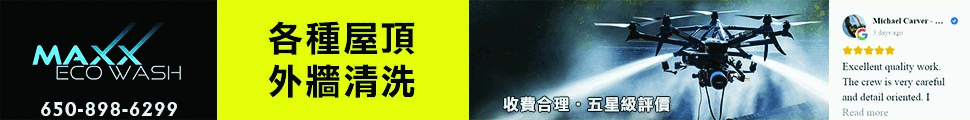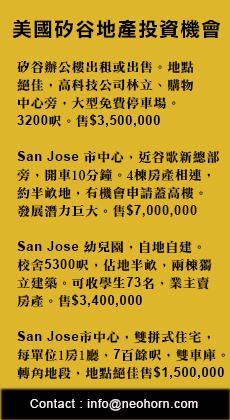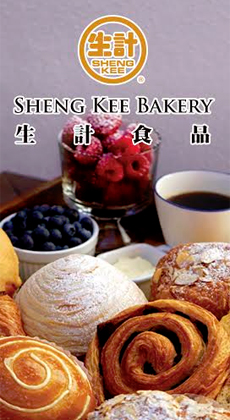去湖南旅遊,長沙的天心閣是必遊之䖏,它與古城牆、
前些天,朋友傳來的「麻將也瘋狂」照片集,
幾年來,走過大陸一些城巿,雀戲的人無所不在,
看到大陸那種壯大場場面,台灣來人無不嘖嘖稱奇,
1969年在金門服預官役,被借調到明德訓練分班作教官,
小的時候,常去接打麻將的母親夜歸,寡母不願兒子習賭,
金門歸來不久,就體會麻將的樂趣了。那時已在所學專業的地方工作
誰料這一試手,成了嗜好,固定的牌友、定期的相約,
二年多後,牌友之一調職僑委會,去國奉派海外,班子散了,
小心點就是,
來美後,開餐館爲稻粱謀,聽說餐館老闆都陪員工賭錢,
扯這些個人瑣事,是證明不再打麻將的我,
或有人不以爲然,擧有傷國體、有礙觀瞻爲辭,其實,
有報導說,多打小麻將,可緩延老人失憶症的出現;唉,人老了,
文/ mike H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