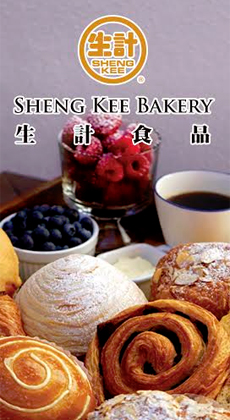舊金山的海鮮名聞全球,舊金山有一種魚,叫做「崇魚」,是舊金山海鮮中的珍餚,據說,崇魚比鰣魚肥,比鯽魚嫩,比石斑鮮,清蒸崇魚,是舊金山的中國菜中的名饌。
我到過美國三次,在美國的城市中,以舊金山到的次數最多,待的時間最久,當朋友們發覺我居然始終沒有嚐過崇魚的美味,大為驚奇,特地在一家以崇魚烹調最有名的中國餐館中宴請我。
那天的菜式,十分豐盛,在外國能吃到這樣的中國菜,真是十分意外,崇魚是最後的主菜,雖然那時我早已吃飽,但著名的崇魚實在鮮美,在主人慇勤的招待下,我不斷的吃,吃了好多好多。
大家都在贊美那天的崇魚特別新鮮,有一位席間的朋友説:「崇魚實在好吃,只是魚刺太多太細,一不小心就會鯁在喉中!」
我也發現魚刺太多太細,不幸,我更發現有一根魚刺已鯁在我喉中, 既然我是主客,實在不好意思把這件事説出來,心想:一根魚刺有什麽了不起,吞幾口飯下去,不就行了嗎?其實,我最不會吃魚,常常把魚刺鯁在喉中,吞飯是很有經驗的。
但著名的崇魚,不同凡響,這根魚刺特別有個性,我幾乎「偷偷地」(不便被人發現)把一碗飯吞完,它還是固執的霸佔在我喉中,更尷尬的是,在我右座的陶伯伯對我關懷備至,一看到我「猛」吃白飯,料定我尚未吃飽,竟給我左一匙「麻婆豆腐」,右一匙「冬菇菜心」,不住説:「吃飯要配點菜,這個菜最下飯!」
於是,我只得連「菜」帶「飯」,「囫圇」吞之,心裏是「有苦說不出」,嘴裏是「有刺吐不出」,又想到「醋」是去刺的良方之一,再偷偷喝了一點醋,一時間,嘴裏酸甜苦辣,什麽滋味都有,而那根魚刺還是無動於衷。
最後,總算磨菇到終席,侍者送上了「幸運餅」,我的那個脆餠中的小條上寫著:「當你需要朋友的時候,朋友就會在你身邊。」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但也有一根魚刺牢牢地刺在我喉中。
我生平最恨人「小題大作」,決心「按刺不動」一切等回到旅社,再慢慢想辦法,我就不信我解決不了一根「魚刺」,於是,我依然笑嘻嘻的(可能笑得有些勉強)和朋友們「談笑風生」(可能談得心不在焉),好不容易,總算「賓主盡歡」,席終人散,我被鄭先生夫婦送回了旅社。
到了旅社,先攬鏡自視,張大了嘴,往喉中深深看去,哇,可不得了!一根又長又細的魚刺,正一半插在喉中,一半露在外面,看得到,但是摸不到,我發了橫心,非弄出來不可,拿兩支原子筆當筷子,到喉中去又探又掏,弄得滿身大汗,那根刺絲毫不動,而喉嚨愈來愈痛,我一急,坐在床上,只差沒哭出來,心想,在台灣,我可以找個醫生,給我鉗出來,偏偏在美國,人地生疏,怎樣是好?
坐在床上發了半天呆,我終於「投降」了,只好忍痛打電話給朋友,也是飯局的主人:「還記得我那個幸運餠中的小籤條嗎?」
對方楞了一愣,立刻恍然大悟,有些著急的問:「我們馬上來,但是妳到底怎麽啦?」
「其實也沒有什麽,只是有一根崇魚的魚刺刺在我喉嚨裏!」我還故意輕描淡寫,「問問你們有什麽偏方可以取出來?」
「怪不得大家發現妳猛吃白飯,我還以為菜不好,妳沒吃飽呢!」(原來大家都發現我在「吃白飯」哪!)
「妳有沒有試過吃麵包?」
麵包?一語提醒夢中人!到樓下餐廳,慌忙買了兩個硬麵包,左吞右吞,麵包吞完,依然無效,心想凖是麵包太硬了,又買了兩個軟麵包,當兩個軟麵包下肚,我的胃已快「爆炸」,而那根魚刺依然「固守崗位」、「攔喉而立」!
一會兒,朋友們趕來了,陶伯伯、中原等都來了,大家左一句右一句的貢獻意見,中原説:「有位王畫家説:喝醋最有效!」
「喝過啦!」我愁眉苦臉的。
「再喝一點也無妨!」鑫濤説,他和我是一起來美的,對我十分照顧。
於是,再到樓下餐廳去要醋,那餐廳的侍者,對我從上到下直望,大約怎麽也弄不清楚,我這個東方女人,怎麼吃得如此古怪?硬麵包、軟麵包、再加上一杯白醋!
閑話不提,那杯白醋又下了肚了,天知道!美國醋有多麽難吃!酸得簡直不可思議,沒有把那根刺化掉,卻差點把我的牙齒都酸掉了。
「我看,」陶伯伯簡單明瞭的説:「去醫院掛急診號!只有醫生有辦法!」
去醫院?掛急診?為了一根魚刺?我堅決反對!但是,朋友們當機立斷,一方面打電話去醫院聯絡,一方面我被「強制執行」。
無可奈何中,我被送到了一家好大的醫院門口,穿過長長的走廊,往急診處走去,陶伯伯,鑫濤及中原都陪著我。
我站在急診處的掛號台前,心裏可又慚愧又好笑又彆扭,一根魚刺!僅僅是一根魚刺!這樣勞師動眾!尤其,我最恨「小題大作」的人!
急診處有位年輕的美國醫生,中原簡單的告訴他我喉中有根「魚刺」,那醫生點點頭,取出一張好大好長的表格要我填。
我一看那表格,姓名、籍貫、年齡、父親名字、母親「中間」的名字,(幸好我母親的名字有三個字,如果像我一樣是單名,我真不知道這「中間」名字如何填法?)地址、美國親友名、我的血型……天哪!這表格比我在台灣的戶口名簿還詳細!怎麽填得完?我求救的望著朋友們。
「她只有一點小小的麻煩,喉頭有一根小小、小小的魚刺而已。」鑫濤對那醫生解釋。
「表格還是要填。」醫生一本正經的説。
沒辦法,填表格!
這一填填了半小時,好不容易填完了,那位醫生開始問問題:「妳以前害過什麽病沒有?」
「妳做過盤尼西林試驗嗎?」
「妳對藥物會不會過敏?例如麻醉劑?」
我的英文不行,這些話都要鑫濤和中原翻譯給我聽,我越聽越害怕,對鑫濤説:「他到底要把我怎麽樣?如果是在台灣,一位護士拿把鉗子就夾出來了!」
於是,鑫濤再對那醫生強調了一次,這「魚骨頭」是「小小、小小、小小」的,這麻煩也是「小小、小小、小小」的。
那醫生的臉色卻更沉重了。
「好,你們請在外面等,病人到手術室來!」醫生對我説。
手術室!我嚇了一跳,為魚刺進手術室,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沒辦法,只得硬着頭皮進去,一張好大的手術檯,一頂大大的手術燈,醫生命令我坐到手術檯上去,我照辦了,一時間,那醫生好忙好忙,一位護士也進來幫忙,大燈、小燈、探照燈都推到我面前來了,然後,護士又推進來一輛小車,我一看,車上有個大大、大大的盤子,盤子裏整整齊齊的排列着大刀子、小刀子、大鉗子、小鉗子、大剪刀、小剪刀、大針管、小針管……
天哪!看樣子他們準備切開我的喉管來取那根魚刺呢!我大驚之下,慌忙對那年輕醫生説,我不懂英文,非把我的朋友請進來不可!
鑫濤進來了,我心慌意亂的説:「魚刺不拿了,咱們走吧!」
鑫濤一看這「架勢」,也呆了,再度對那年輕醫生強調了一次,那魚刺是多麽多麽「小小」的。
「越小越麻煩,」那年輕醫生説:「你們別急,我已經打電話給專門醫生去了,那醫生馬上趕來!」
什麽?還要另請醫生嗎?鑫濤也急了,問那年輕醫生可否由他動手,年輕醫生大大搖頭:「這怎麽行?我不是喉科大夫!」
我坐在那兒,和鑫濤面面相覷,怎麽也沒料到美國醫院是這樣「慎重」的!鑫濤悄聲問我:「妳那根魚刺到底還在不在喉嚨裏啊?別大張旗鼓的掛急診號,請專門大夫,等醫生到了,妳那根魚刺已經不在喉嚨裏了,那就更鬧笑話了!」
一句話提醒了我,真的,自進醫院,我被這些表格啦,手術檯啦,探照燈啦……已經攪昏了頭,根本沒有再去注意喉嚨裏的感覺,萬一那魚刺已不在了呢?剛剛在旅社,我是千方百計要把魚刺弄掉,現在可暗暗禱告,魚刺可別不在了!我急忙咽口水,還好,魚刺仍然鯁在那兒,我鬆了口氣,十分「安慰」的對鑫濤説:「還好還好,魚刺還在!」
坐在那兒等「專門」醫生的時候,我開始和鑫濤研究這根魚刺的「價格」,我説:「看樣子,沒有一百美金的診療費,這魚刺是擺不平的!」
「即使不到一百,也要八十!」
唉!舊金山的崇魚!我服了你!
「專門」醫師終於到了,果真很有氣派,和那年輕醫生大大不同!高個子,年近五十,留著小鬍子。
一進來,先聽取年輕醫生的報告,看我所填的表格,檢查盤子裏的器具……立刻,他發了脾氣,對護士高聲責備,器具裏缺少了「壓舌器」!
護士慌慌張張的跑出跑進,「壓舌器」來了,又少了「彎鉗」,好不容易,東西齊全了。
醫師命令我張開嘴巴來,彎鉗伸進了我的嘴,在我正研究着他會不會動用那些剪刀針管的一剎那間,鉗子從嘴中取了出來,上面牢牢的夾著我那根又長又細的魚刺!前後「手術」時間,三秒鐘!前後「進院」時間,兩小時!
「好了!」醫師説,很正經,很嚴肅的,「為什麼説是小小的刺?很大呢!要知道,刺越小越麻煩,我曾經為一根魚刺動過大手術!因為那根刺斷在喉肉裏,引起了嚴重的發炎。還有個病人,把刺咽進肚子裏,刺穿了胃壁!不要以為一根魚刺是小麻煩!」
我「洗耳恭聽」,「心悅誠服」,尤其是「無刺一身輕」,初次領教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意義。從手術室出來,那專門醫師又開了一張單子給我,上面寫著三位喉科醫師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如果明天喉嚨不舒服,可以找其中任何一位!」
我收了單子。診療費開出來了,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只有十八元伍角!再看急診的最低費用,是十七元!如此大張旗鼓,只收了一元伍角的「手術費」!不禁使我愕然,心想,在台灣,一根魚刺不會弄到「請專門醫師」,如果「請」來了,就不止收費一元五角美金了!
一根魚刺,使我領略了很多的東西,中外作風的不同,海外友人的溫暖,(第二天,我曾參加了中華聯誼會的晚宴,大家紛紛向我「慰問」這「魚刺之災」)以及,一個教訓,「小」問題也會有「大」麻煩!
話說當晚回到旅社,我的「喉嚨」已無問題,但是,胃卻有些作怪,想來想去,那些白飯、硬麵包、軟麵包、中國醋、外國醋……一定都在胃裡搗蛋。
臨睡前,我吃了四粒消化藥,三粒中和胃酸藥!
事後,我又去吃過兩次崇魚,很小心的吃。 至今,我仍認為,世間美味,莫過於「崇魚」!
文/瓊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