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綱
劉和平的叔叔在逃荒途中餓慌了,他躺在樹下休息,陷入昏迷中。劇痛將他刺醒,睜開眼,發現一把鐮刀,正在“收割”他的屁股。與他同樣飢腸轆轆的災民,準備食人肉來充飢,清醒過來的他僥倖逃過一劫。這是十年前,作家劉震雲和導演馮小剛在河南鞏義市聽聞的故事。故事的講述者劉和平當時已經90歲,她的聲音從掉光了牙齒的口中穿越出來,回到70年前。那一年,她所在的300多人的村莊,大概餓死掉一半。她本人在經歷與親人的生離死別之後,被外國人主持的教會挽救了生命。
1941-1943年,類似的因飢餓而逃荒、死亡的場景,遍布在河南省的每一個角落。水旱雹霜風蝗災情下,政府仍堅持不切實際的軍糧徵購,並極力封鎖消息,賑濟乏力,最終導致了高達300萬-500萬人的死亡事件。
這起人間悲劇,發生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在相當長時間內,一直被史家所忽略。 1961年12月,河南省政協副主席張仲魯(1942年為河南省政府建設廳長)撰寫的《1942年河南大災的回憶》,和1970年台灣《春秋》雜誌刊發的楊卻俗(1942年為三青團河南許昌分團幹事長)《憶民國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等文章,較早披露了1942大饑荒的珍貴信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作家劉震云的作品《溫故一九四二》,讓更多人知曉了那一段歷史。
劉震云的作品被馮小剛看中,最終把它變成了一部電影。 11月11日晚,《一九四二》在第七屆羅馬電影節首映。電影不可避免有虛構的細節與橋段,真實的1942年河南飢荒又是怎樣的?
人倫悲劇:政府隱瞞不如實上報
餓殍遍地當時的河南省政府卻致電糧食部雲:“河南人民深明大義,願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徵實徵購均已超過定額”
洛陽火車站擠滿了逃難的災民,他們在警察木棍或拳頭的毆打下,偷偷穿越月台,爬上不知駛向何處的火車頂棚,只為離開這飢餓的故鄉。 《大公報》戰地通訊員張高峰穿過瘦得暴露出一根根血管的乞討手臂叢林,想要幫助災民取得賑濟委員會的圖章,但是失敗了,他擠不進那被幾百人團團圍住的“難民登記站”。
1942年12月,不要說正常的食物,洛陽附近各縣市連樹葉都已經很難找到,樹皮也被剝光吃了。一路走來,張高峰看到十室九空,甚至乾柴都被搗碎用以果腹。他看著身邊災民一個個倒地不支,卻無計可施。瘦過之後,災民們開始變得浮腫起來。有人鼻孔眼角處已經明顯發黑,那是因為食用了一種名叫“黴花”的有毒野草。
1941年的水災剛過,1942年春,河南各地又開始經歷冰雹、黑霜與大風。而更為普遍的是大旱,旱後蝗蟲開始肆虐。此時的河南,北、東和東南部分地區已經淪陷,作為對日作戰的前線陣地,國民黨河南駐軍每年要從農民手中徵購大量的糧食。天災來時,農民手中僅有的餘糧被搜刮殆盡。
災情並沒有如實上報中樞。據楊卻俗回憶,許昌縣長王恆武年初預報農收為八成,但災情遠超預料之外,王恆武卻不再據實以報,仍按原定預報徵收糧食,如果繳不夠糧,地方自衛團的團勇就在農民家裡坐吃不走。
許昌縣長不據實徵糧,應和時任河南省長李培基的態度有關。 1942年任河南省糧政局秘書的於鎮洲事後回憶,許昌及周邊數十縣份,曾紛紛報災,但省政當局卻認為各縣為逃避多出軍糧,故意謊報。查核過程中延誤了時間,也因此沒有將災情轉報中央。
災情已經嚴重到餓殍遍地的程度,河南省政當局難道會無所知悉?事實上,連洛陽司令長官都已經掌握一定實情,但因匯報的材料與河南省府有差異,反而被國民黨中央訓斥為誇大災情。
國民黨政府當時實行“徵實”制度,對虛報災情者予以重懲,對成績好的給予獎勵。據時為軍事委員會軍風紀巡查團主任委員金漢鼎回憶,河南省政府在徵糧上非常積極,曾電糧食部雲:“河南人民深明大義,願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徵實徵購均已超過定額”。可見,對農民的過度搜刮,很大程度上出於政績考量。
《豫災實錄》面對嚴重的災情,國民黨中央代表卻說,“不應對災荒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而亂國際視聽”
“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在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這是張高峰1943年初在《大公報》刊發的《豫災實錄》中的內容。
出現人口市場:出售妻女成常見現象
早在1942年夏末,就已經出現因飢餓而出售妻女的現象。 1940年在陸軍大學參謀班三期畢業的靳士倫,當時正在河南唐河縣源潭鎮駐軍。他注意到,有人販子帶著婦女前往湖北隨棗方向。等到秋末,路上販賣的人數明顯增多,包括他所在的源潭鎮也出現“人市”。
在日軍的凌厲攻勢下,國民政府已在1937年底遷都重慶,那裡距河南大約1000公里。依據現有的證據材料,最早向重慶陳情者應為河南省賑濟會推派的三位代表。據代表之一、原河南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楊一峰迴憶,他們(10月上旬)抵達重慶後,“始知中樞因受省政府謊報災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鄉亦鮮知災情如是之嚴重。”經過他們呼籲之後,國民黨中央才決定推派張繼、張厲生二人前往河南實地考察。
兩位中央大員在洛陽召集了一個會議。據在場的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仲魯說,他倆宣示了“中央德意”,表示應予救災,但不能因此而減免軍糧,同時不應對災荒誇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而亂國際視聽。張厲生還指責視察期間看到的路邊剝樹皮的農民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給他們看”。
但在洛陽以南最嚴重幾個縣視察後,張繼和張厲生也承認存在災情。這之後,河南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10月底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領銜提出《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而後蔣介石決定撥款2億法幣這種貨幣正日益貶值,用作河南的救災貸款。對於河南的旱情而言,這點錢是杯水車薪,中間又經過貪污官員的盤剝(主持河南平糶救災的李漢珍是著名貪官)。而國民政府為了保證軍需,1943年1月,又從河南征收了170萬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麥。
封閉輿論 編制完美謊言
1943年春,正是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時節。
《看重慶,念中原》美國《時代》周刊駐亞洲特派員白修德說,“沒有任何一種殘暴會超過河南大災”
國內的媒體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對河南飢荒保持沉默。在全國范圍內造成影響的第一篇報導《大公報》的《豫災實錄》,刊發在1943年2月1日這已是張高峰完稿半月之後,而後該報又發表王芸生撰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呼籲重慶政府根據國家總動員法,嚴厲管制一切物資的生產集中與分配。蔣介石暴怒,大公報因此在2月3日至5日被勒令停刊3天。張高峰本人則在一個月後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以“共產黨嫌疑”逮捕,並無實據,他在軟禁期間逃脫。
國內媒體表現最佳的實際上是1942年創刊的河南《前鋒報》,該報1943年2月至5月,連續刊發李蕤(筆名流螢)十餘篇災區通訊,及70餘篇社評。據李蕤之女宋致新介紹,河南省新聞檢查處,同樣對《前鋒報》發出停刊3天的命令,但報社拒未執行,這也許是因為《前鋒報》所在的南陽屬於宛西自治政權,也許由於社長李靜之與上層人物的關係,也許由於該報沒有《大公報》那樣大的影響,原因不得而知。而河南飢荒在國際上引發關注,則有賴於美國《時代》周刊駐亞洲特派員白修德的報導。 1943年3月22日,他撰寫《等待收成》刊發時,宋美齡正在美國四處演講,她要求《時代》周刊老闆亨利·盧斯解僱白修德,被拒絕。
白修德隨後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與蔣介石作了會面。 “用僵硬的握手錶示禮節後,(蔣介石)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白修德晚年在回憶錄中稱,蔣介石起初否認白修德的一些說法,直到他拿出狗吃人屍的照片。
“是河南的大饑荒,使我的立場從站在(支持蔣介石的)陳納德一面轉而變得站在了(反對蔣介石的)史迪威一面。”白修德深信,蔣介石“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如史迪威將軍所說的那樣;而且對他的人民也同樣毫無用處,這一點才是更加重要的。”
從目前公開的蔣介石日記看,他沒有記錄有關河南大饑荒的信息。上海市委黨校教授朱華曾考證蔣介石中山艦事件日記不同版本,認為他不斷修改自己日記,主要是為了塑造自己完美的人格形象,因為他已準備將日記公之於世。
1942年,蔣介石政權失去民心的徵兆已經顯露。白修德說,“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我也會像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但沒有任何一種殘暴會超過河南大災。 ”
此巨片將於11月30日在灣區下列各戲院盛大上映。
San Francisco/Bay Area
3111 Mission College Blvd., Santa Clara, CA
Cinemark Century 20 Great Mall and XD
1010 Great Mall Drive Milpitas, CA
Cinemark Century 25 Union Landing and XD
32100 Union Landing Blvd,, Union City, 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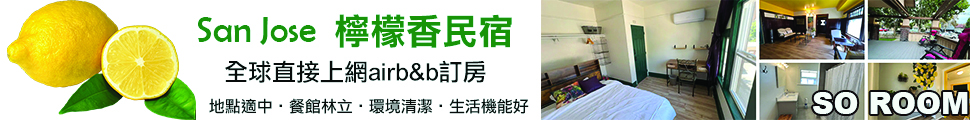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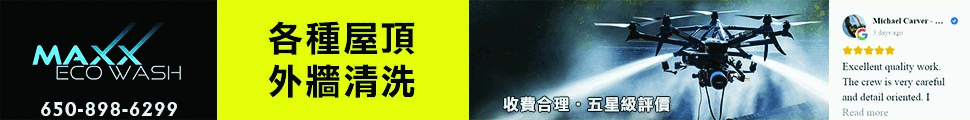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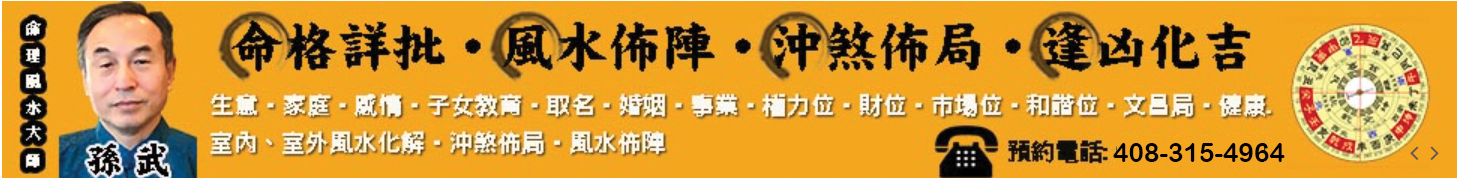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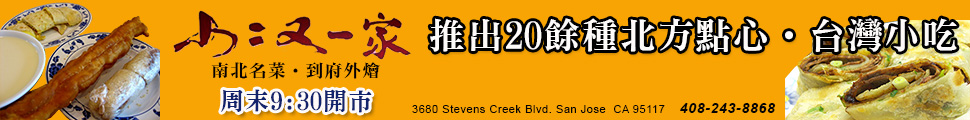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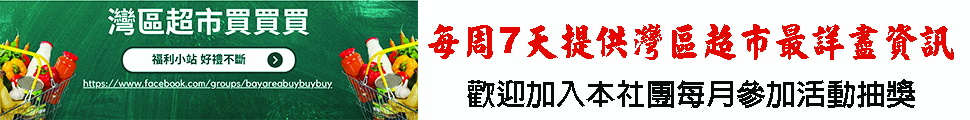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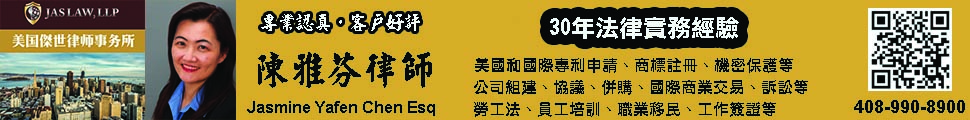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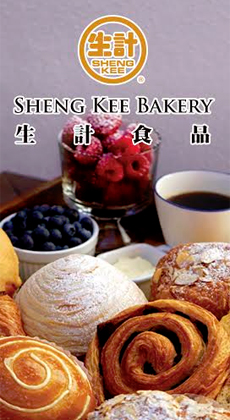
这个惨剧,已经令人唏嘘不已!可是还相对有人说得。后来的惨剧饿死几千万,更加惨不忍睹,而且无任何外来战乱,更加无话可说了。希望悲剧不再演,人类更加有爱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