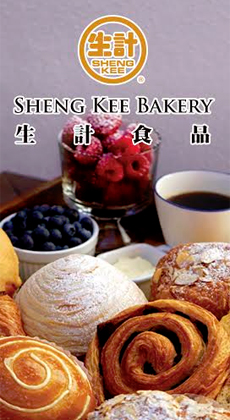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號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前書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花錢混入了” 華人幫” 團隊。工人們簽署了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三桅大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上船幾天後,大帆船終於從舊金山出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風暴來襲。每天僅能吃兩頓劣質食物,僅能有一杯水。高大魁梧的白人漁夫們在船上變成水手,斯特恩見識到他們的工作和個性,也認識了華人包商手下” 華人幫” 的烏合之眾。賭博、走私、剝削、疾病、危險、與死亡無時無刻地伴隨著這些人與” 地獄之船” 駛向遙遠的北方。
他們花了四週橫渡了 1600 英里寬闊的海洋,通過一個僅十英里寬的烏尼馬克海峽進入浪濤洶湧的白令海。終於,在古老的移民定居點努沙加克附近,他們拋下錨。幾天後,他們轉上駁船,在午夜時分被帶到上游的罐頭廠。在昏暗的暮色中,一群瑟瑟發抖的華人幫終於從駁船上蹣跚地下了碼頭。抵達阿拉斯加後,斯特恩在條件最惡劣的罐頭廠工作,獲得了第一手的調查資料。
上篇摘要: 我在阿拉斯加待了大約三個星期,目睹了最糟糕的罐頭工廠裡面的生活。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一行業的情況,我必須參觀更多的罐頭工廠。因此我必須「逃離」我的華人老闆並搭蒸氣船回去。布里斯托爾灣每月只有一次的逃離的機會。這是一艘是從蘇厄德(Seward)出發的小蒸汽船——送郵件的船。
第29章 斯特恩,跟隨罐頭船隊兩個月,欠 14.80 美元

圖解: 正在用魚叉轉送鮭魚。從早上 6 點到下午 6 點,人們站在深至雙膝的鮭魚中工作,每小時 65分錢美元 。
連續幾天,我都徘徊在希望與恐懼之間。
我必須逃離這家罐頭廠,好幾次我被告知這樣的事從來沒有人做過。我必須有一個特別好的藉口,還有足夠的錢和好運。即便如此,那也只是一個機會。
在離開舊金山之前,我已經事先和我的妻子安排寄一封「假」信,說明她突然生病,並催促我盡快回來。她照做了,純屬巧合的是這封信己透過利比、麥克尼爾和利比的一艘蒸氣船送達到我手中。
這是我在阿拉斯加收到的唯一的一封郵件,它拯救了我。信中說,我的妻子在一次車禍中受了重傷,催促我趕緊回家。這封信是由她母親簽名的,信中並提到已附上回程的費用。
「從來沒有人做過」
我在工作營地傳播這壞消息,扮演了哈姆雷特這個悲劇性的丹麥王子的角色。最後我把事情告訴了班。他看不懂英文,所以我把信唸給他聽。他一如既往地表現出善意的同情心,但他還是懷疑地搖了搖頭。
「從來沒有人做過,」他說。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也知道契約——鮭魚很快就要來了。無論如何,自從墨西哥人死後我們就缺一個人手。」不過,他承諾將與華人老闆的代表商量一下。
在此期間,我每天都在為公司工作。我們團夥中有幾個人為了每小時 25 分錢的工資而發起了罷工。
只有一個黑人,家裡有個妻子要養活,和我還在工作。我擔心沒有足夠的錢買斷契約和買回程票,所以需要我能賺到的每一分錢。我急於想知道票價是多少,有一天,當我在碼頭盡端時,當我正要跳進公司的一艘拖船上,向一位老水手打聽前往西雅圖的船費。我腳還沒有碰到甲板,赫克托就出現在我上方。
被「斥責」
「你在那裡做什麼?」他對我大喊。「這就是你搬運木材的方式嗎?你最好去工作,否則你就沒有工作了。 」
大約在這個時候,漁民們已準備展開今年度的出海捕魚之旅。船隻已經重新上漆,差不多裝滿了補給品。
有一天,北歐人發現義大利人私有的漁網的網目比他們使用的公司漁網小一英寸。他們威脅要罷工,工會會員並召開了會議。一天早上,漁民們聚集在他們的宿舍前,互相激烈地爭辯了幾個小時。
一度看起來捕魚就要停止,但最後義大利人同意不使用他們的小網目漁網,問題就解決了。
春天和蚊子的到來
天氣轉變得溫暖並持續了好幾天。我們發現在阿拉斯加,大自然既能撫慰也能懲罰,春天真的來了。
然而,隨著氣溫的升高,蚊子也隨之而來,而且隨著夏季的臨近,蚊子數量也大為增加,構成一種比寒冷和潮濕更為悪烈的煩擾。
許多晚上,我們的音樂會依然在簡陋的小屋裡進行,炭火產生的煙霧正好驅走了蚊子。
在這些聚會中,室內娛樂的一部份便是講述像我這樣試圖逃離華人幫的人卻以失敗告終的故事。我們的夥伴中沒有一個人相信我有可能解除契約並「擊敗它」。
獲得許可
有一天,班告訴我,那個中國佬要跟我談談。我走進了他的「辦公室」,那是我們宿舍後面的華人商店,心都提到了嘴中。他一如既往地面帶微笑,但他並沒有任何意思讓我離開。
我讀了這封決定命運的信給他聽,並解釋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留在阿拉斯加,我會很自然地成為他手下的一個很差勁的罐頭廠工人。
「好吧,」最後他同意了。「你把你欠梅耶和我的錢都付清,我就讓你走。」
他拿出毛筆開始計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緊張的時刻。
欠 14.80 美元
距離我在舊金山的船上簽約已經過去兩個月。我每月的薪水是34 美元。他承認欠我 68 美元。
我欠梅耶 62.50 美元的裝備費。中國佬會向我收取 5 美元用於繳納阿拉斯加政府學校稅。中國佬預支了我十美元,我已經花掉了,我在華人和墨西哥商店花了5.30美元。
這樣一來,我總共欠了中國佬和梅耶82.50 美元。從我欠他的 82.80 美元中減去他欠我的 68 美元,我發現我還欠他 14.80 美元,為此他立即開出了一張賬單。
我在船上墨西哥和華人商店的帳單己經相當小。除了我預支拿到的十美元之外,我只花了 5.30 美元,比同夥其他大多數工人都少。
你能贏嗎?
然而,即使工作了兩個月,我仍然欠我雇主14.80美元。
「也好,」我對自己說,「我現在辭職是件好事。如果一個人工作兩個月後欠雇主 14.80 美元,那麼五個月後他會欠他雇主多少錢? 」
墨西哥人常用一句話來形容阿拉斯加鮭魚的罐頭包裝工作——「mucho trabajo, poco dinero.(工作多,錢少。) 」這似乎還算是一種很溫和的說法。
我對流動工人和他們的工作了解不多,但我非常懷疑在美國任何地方是否有那個行業需要一個工人工作兩個半月才能真正開始為自己賺錢。
我整個捕魚季節收入的一半左右已經沒有了,而我唯一的收穫只有在梅耶那買的廉價裝備。工作服已經破爛不堪,我也不得不把鞋子送掉。即使我繼續幹流浪漢這一行,我也絕不會隨身攜帶這套床墊和被褥。
我沒有襪子,也沒有我花錢買的羊毛外套。只有那半棉「羊毛內衣」、半棉襯衫以及搶眼的綠黃相間的帽子代表了我全部的投資。
華人老闆的利潤
我有點諷刺地感謝了那個中國佬。我的離開對他的大老闆來說就如天鵝絨——一筆輕鬆的利益。他已經從死去的墨西哥人身上淨賺 170 美元,也將從我身上淨賺 102 美元。
但我感到一種深深的寬慰。我已經完成了前所未聞的事情,而且我自由了。我畢竟在捕魚季節的前夕辭掉了阿拉斯加華人幫的工作。如果我的同事們有錢,我可以橫掃全部賭我永遠不會成功的賭注。
口袋裡揣著收據,我終於可以自由地離開阿拉斯加了,但我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我要做一個像《湯姆叔叔的小屋》裡「跨越冰面的麗莎」。
郵船將在幾天之內在河下游十英里處靠岸。我要如何到達那裡?在船抵達以前我該住在哪裏? 在我和我的解救之間有十英里的水域或幾乎無法通行的沼澤,我感覺就像一個被困在一個孤島上的水手。
那天晚上,當我坐在煤堆上沉思時,有一個人像古希臘劇塲用的道具「機器裡的神」一樣地走了過來。我的老朋友和恩人,水手湯姆。
下週預告: 第30篇 「漁夫把鞋子丟進海裡,為漁季贏得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