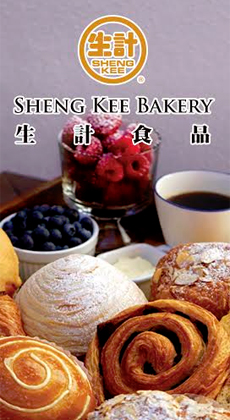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號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前書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花錢混入了” 華人幫” 團隊。工人們簽署了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三桅大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上船幾天後,大帆船終於從舊金山出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風暴來襲。每天僅能吃兩頓劣質食物,僅能有一杯水。高大魁梧的白人漁夫們在船上變成水手,斯特恩見識到他們的工作和個性,也認識了華人包商手下” 華人幫” 的烏合之眾。賭博、走私、剝削、疾病、危險、與死亡無時無刻地伴隨著這些人與” 地獄之船” 駛向遙遠的北方。
他們花了四週橫渡了 1600 英里寬闊的海洋,通過一個僅十英里寬的烏尼馬克海峽進入浪濤洶湧的白令海。終於,在古老的移民定居點努沙加克附近,他們拋下錨。幾天後,他們轉上駁船,在午夜時分被帶到上游的罐頭廠。在昏暗的暮色中,一群瑟瑟發抖的華人幫終於從駁船上蹣跚地下了碼頭。抵達阿拉斯加後,斯特恩在條件最惡劣的罐頭廠工作,獲得了第一手的調查資料。
上篇摘要: 在我們抵達的第二天,我們就埋葬了墨西哥老人。這是一場極為簡單的儀式。對於一個來自陽光充足的墨西哥人來說,這是一張冰冷的床,但卻是他疲憊的老骨頭的安息之地。原住民印地安人須要工作,當春天鮭魚罐頭船抵達時,男人就會過來尋找工作。阿拉斯加政府希望每個罐頭廠老闆都能盡到自己的責任,無論是否真正需要,每個原住民都會被雇用。另一方面,華工也被華人老闆保護。
第26章 斯特恩在三名黑人的協助下組成了四重唱

圖解: 罐頭工廠和漁船隊。這些小船正是漁夫們在這布里斯托爾灣危險水域中勇敢出海的工具,因此你得以吃到罐裝鮭魚。每年都有幾個勇敢的拉丁人和北歐人喪生。
我們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 6 點到晚上 6 點。中午,當我們吃完一天的主餐後,我們有半小時的休息時間。我們的工作時間並非工會標準,我們每天工作十一個半小時,包括星期天,直到鮭魚開始洄游。之後時間就更長了。
我們的下一份工作是製作罐頭。錫板已隨船運到,而我們這些華人幫成員則負責操作製罐機器。
罐頭廠的建築到處都有大裂縫,寒風從這棟像穀倉般的建築中穿透進來,使我們在船上患上的感冒遲遲無法痊癒。
測試罐頭
記得有一天,我在罐頭工廠裡面試圖點燃我的煙斗,但透過裂縫進來的冷風吹滅了我的火柴。
我的工作是測試罐頭。我會站在一個裝滿熱水的小水槽前,將做好的罐頭放入一個籃子裏,然後用腳踏板將其浸入水中。
蒸氣會自動噴射到水下面的罐頭上,如果有任何漏氣,水面就會出現氣泡。通過這種方法,可以確定製罐機是否生產出完美無缺的罐頭。我面前有熱騰騰的蒸氣,背後有冷風襲來,我的感冒幾乎沒有痊癒的機會。
被華人喚醒
這幾天我們的每天的作息大致如下:早上5點15分,華人廚師查理會進入宿舍來叫醒我們。
他會用一種粗啞、刺耳的聲音喊出一些話,聽起來像「Bundle o’ hay」。我們理解這句話在華語的意思是「該起床了」。這給了我們 15 分鐘的時間穿衣和漱洗。早餐的汽笛聲在5點30分響起,伴隨的總是哈士奇狗群奇怪的嚎叫聲。
無鹽的玉米糊,上面覆蓋著「西南奶」,並加了一點糖、雜燴、或豆子,還有馬鈴薯和咖啡被端到了長桌上。我們通常會穿著大衣站著吃早餐。在我們吃完之前,食物就己經變冷了。
供應腐敗的奶油
我們剛抵達時就被承諾會供應奶油。幾天後,奶油真的上桌了,但已經腐敗到無法食用。麵包倒是還不錯,因為負責烘焙的師傅「餅乾」有一個好爐子可用。
我們現在最需求的是足夠的牛奶來配咖啡和玉米糊、多汁的蔬菜、足夠的糖和水果。
嚴格來說,直到鮭魚潮開始,肉才變得可以入口。通常我們吃的是鹹牛肉,硬到無法咀嚼,味道重的無法享用。我們每人會拿幾塊,然後把它們拿去餵給雪橇犬。這樣我們就避免這些肉在下一餐時以雜燴的形式再度重生。
早餐後,我們會在鍋爐房停下來一兩分鐘取暖,吸幾口煙斗,然後回到我們的機器旁。
與船上一樣,罐頭廠也存有雙重標準的生活待遇。漁民們忙著為出海打魚準備裝備,海灘幫正在操作打樁機來建造新的魚倉,而公司的其他員工則在罐頭廠裡忙碌著,好讓機器在經歷一個冬天的閒置後恢復運作。他們的一天也從早上 6 點開始,但他們在 7 點便能停下來吃早餐。
每天下午 3 點,為漁民和公司其他員工提供咖啡和蛋糕的汽笛就會響起。而我們華人幫成員則得繼續工作。
除此之外,公司員工一日三餐都吃得很好。早餐包括薄煎餅、培根、雞蛋、玉米糊等,其他餐點也同樣豐盛。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完美無瑕的桑迪的指揮下送上有油布覆蓋的桌面。
早上在製罐機的永不停歇的叮叮聲中熬過去了,在漫長的時間之後,中午的汽笛聲終於響起。
在連續六小時做一項只需要機械式的重複而不要思考的工作後,那汽笛的聲音幾乎和在「煙霧中的摩西」附近的那聲「陸地」的呼叫一樣悅耳。
先來先吃
我們穿過一條長木板,橫跨罐頭廠周圍護城河般的沼澤地帶,衝向宿舍去吃晚餐。有一天,我一不小心從濕滑的木板上滑倒,跌了五尺,我全身泡在一英尺深的黏答答的積水中。
餐桌上是先來先吃。我們常常趕去時才發現最好的食物已經被吃光了。
偶爾我們會有甜點。它通常是沒放雞蛋或牛奶的麵包布丁,但加了點糖並用了一些葡萄乾一起烤製。有一次,甜點是用蘇打餅乾做的,但由於太不受歡迎,所以再也沒有嘗試過了。
伙食總是以澱粉為主,偶爾小有變化的是一盤包心菜,更少見的是燉肉中加些四季豆或豌豆。
獲取剩菜
當汽笛再度響起叫我們趕回機器時,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填飽肚子。到了晚上六點鐘,我們就完工了,但還沒來得及洗手,晚餐就已經上桌了。這又是快者生存的時刻,所以我們不失分秒地趕回去吃飯。
晚餐後,迎來了當天的第一次的喘息的時間。但我和一個黑人男孩很有默契地承接了一份工作,為丹麥守夜人「優 」鏟煤,「優 」年紀太大了,無法完成他該做的工作。作為回報,他有時會偷偷塞給我們一些桑迪桌上剩下的水果或果醬。
组成四重唱
天色似乎永遠不會變暗,一開始我睡不著。因此,我會到某間小屋裡消磨時間。平日常常下雨,而且總是很冷,但小屋裡卻是乾燥而溫暖的,即使冒著煙的爐子確實讓我們的眼睛發紅。
我們最喜歡的娛樂方式之一是唱歌。我和三個黑人組成了一個四重唱,每天晚上我們都會在一間煙霧瀰漫的小屋裡演唱一長串的歌曲,小屋裡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不同膚色的人。
我們的歌曲大多是懷舊的歌曲,最常被點的都是有關家和母親的歌曲。總是能引起全場轟動的是我們的首席歌手鮑勃的一首獨唱,其中有高低起伏的重複句 《加州,你就是為我而存在的》。
一些古老的民歌中融入了真實的感情,老兄弟山姆·華盛頓在他嘶吼著唱起 《別哭了,我的女士》,都會讓我的背上竄下一陣顫栗。
這是他們的歌
「大男孩」,另一個我們歡樂不起來的「歡樂」合唱團的成員,貢獻了這首有憂鬱旋律和几套不同的歌詞,最後一段我們懷著熱烈的感情唱出:
豐收時的月亮,豐收時的月亮,照耀吧;
哦,豐收時的月亮,豐收時的月亮,照耀吧;
當我死後你會継續照耀。
墓地是一個孤獨的地方;
我說墓地是一個孤獨的地方;
他們輕輕地將你放下,然後把泥土丟在你的臉上。
兩匹白馬並肩奔馳,一人説
兩匹白馬並肩奔馳,一人説
「你奪走了我的女人,希望你滿意。」
海洋中有一個變化,變化在深藍大海中;
海洋中有一個變化,在深藍大海中;
假如我不離開阿拉斯加,我將有所改變。
下週預告: 第27篇 「 季薪170 美元,華人幫每人要繳 5 元學校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