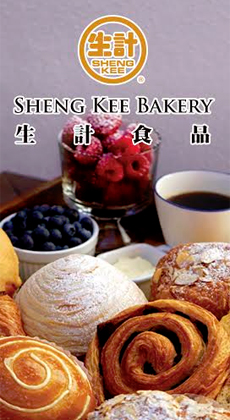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號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前書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花錢混入了” 華人幫” 團隊。工人們簽署了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三桅大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上船幾天後,大帆船終於從舊金山出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風暴來襲。每天僅能吃兩頓劣質食物,僅能有一杯水。高大魁梧的白人漁夫們在船上變成水手,斯特恩見識到他們的工作和個性,也認識了華人包商手下” 華人幫” 的烏合之眾。賭博、走私、剝削、疾病、危險、與死亡無時無刻地伴隨著這些人與” 地獄之船” 駛向遙遠的北方。
他們花了四週橫渡了 1600 英里寬闊的海洋,通過一個僅十英里寬的烏尼馬克海峽進入浪濤洶湧的白令海。終於,在古老的移民定居點努沙加克附近,他們拋下錨。幾天後,他們轉上駁船,在午夜時分被帶到上游的罐頭廠。在昏暗的暮色中,一群瑟瑟發抖的華人幫終於從駁船上蹣跚地下了碼頭。抵達阿拉斯加後,斯特恩在條件最惡劣的罐頭廠工作,獲得了第一手調查資料。
上篇摘要: 罐頭廠建在一片沼澤中的木樁上,部分廠房己陷入了爛泥裡,四周散著大量浮木和垃圾。但更糟糕的是我們自己的宿舍,整個畫面給人一種無法形容的荒廢與破敗。第二天凌晨,墨西哥老人去世了。早餐後我們集體清除了跳蚤。幾天後,我們72個人輪流使用一個小浴缸終於都洗了澡。
第25章 經濟的枷鎖將阿拉斯加罐頭廠工人束縛在工作上

圖解: 罐頭廠的一景,斯特恩說,罐頭廠裡的裂縫和冷風使工人一直處於寒冷之中。前景是罐頭廠華人幫的宿舍。
在我們抵達的第二天,我們就埋葬了墨西哥老人。
這是一場極為簡單的儀式。木匠「奇普」用松木製作了一口棺材,我們幫裡的一個年邁的雅基人做了一個十字架,塗上油漆,並寫上了一段墓誌銘。
關島籍的副工頭喬在泥地裡挖了一個墳墓,我們十幾個人圍著那懸崖上小墓地的坑洞站著。
一陣潮濕、寒冷的風從北方吹來,掃過那兩岸被積雪包圍的泥濘河流,吹彎了我們周圍苔原上枯黃的長草。天空陰沉,正飄落著幾滴細雨。
倉促下葬
我們時間緊迫,於是用兩根舊繩子迅速將棺木降下。當它下降時,我們匆忙地摘下了帽子。喬抓起一把泥巴撒在棺材上。接著泥土一鏟一鏟迅速地堆了上去,一句話都沒有說,葬禮就結束了。一名華人幫成員就這樣告別了人世。
地平線上又立了一個白色的十字架。上面寫著:
何塞·梅托雷姆
法萊西奧
1922 年 5 月 23 日
新區,索諾拉州
對於一個來自陽光充足的墨西哥的人來說,這是一張冰冷的床,但卻是他疲憊的老骨頭的安息之地。
“他過得更好”
「他比我們其他人都過的好。」當我們魚貫下山回到我們的小屋村時,老雅基人用西班牙語嘆道。沒有一個罐頭廠的白人參加葬禮,也沒有任何錘擊聲為此停頓下來。鮭魚罐頭廠的老闆們沒有時間感傷。
太陽升起,我們華人幫一夥人也跟著出來了。他們還沒有開始做任何工作,但梅耶給他們的連身工作服裡面的接縫處幾乎全裂開了。有幾個人正忙著縫補他們的衣服,但有些衣服已經破的無法修補了。
我們去了工廠的雜貨店,發現我們可以花 1.9 美元買到一件比梅耶在舊金山以 2 美元的價格賣給我們更好的連身工作服。
鞋子也開始出問題,儘管我們大量用油擦拭保養,但它們仍然像篩子一樣滲水。
這是一套「釀酒術」
當我們在宿舍前閒坐時,我們很榮幸地獲得了印地安老酋長的造訪。他到達時己是酩酊大醉,他帶來了一張非常臭的水獺皮,想賣掉它來買一些我們帶來的私酒。
這位古怪的原住民(Siwash)有一套「釀酒方法」。透過適當的處理,他能夠將自己變成一個人類蒸餾器。早上他會吞下一杯棕色麵粉、一杯糖蜜、一杯溫水和一點酵母。然後他會坐在陽光下,讓大自然完成剩下的事。到了中午,他的體內已經足夠發酵了,讓他能反抗他的妻子,一個巨大鬥雞眼的印地安女人,在酋長清醒的時候,她被公認為是真正的酋長。
印地安人要工作
阿拉斯加這一地區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據說有一半愛斯基摩人和一半日本人的血統,是一個懶惰而短見的種族,但他們除了豪豬、雷鳥、兔子、魚類和其它他們射殺、誘捕和捕捉的獵物之外,還必須吃一些其他的食物。
他們的菜單上有一點麵粉、罐裝牛奶、糖,甚至咖啡,標誌著他們進入了白人文明的第一個階段。因此,當春天鮭魚罐頭船抵達時,男人們就會過來尋找工作。阿拉斯加政府希望每個罐頭廠老闆都能盡到自己的責任,無論是否真正需要,每個原住民都會被雇用。
我和幾個年輕的印地安勇士們一起工作過幾天。他們每天的工資是 3 美元,還包食宿,他們在漁民的食堂吃飯。我每天的收入只略高於 1 美元,而且我在中國佬的食堂吃飯。如果我幹的活比不上這兩個小伙子的總和,我早就辭職了。
華人薪水更好
同樣的情況也在中國佬身上也可見到。我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駁船上卸貨,把華人的補給品搬到「清客商店」裡。這有時是一項極其勞累辛苦又吃力的工作,要搬運一箱箱培根、罐頭食品、一袋袋馬鈴薯和豆子。
那天只有少數幾個中國佬願意出來幹活,而那些人絕對不是黑人或墨西哥人的對手。多年來的不事勞動、飲茶與吸鴉片已經削弱了他們中的佼佼者。他們根本無法勝任重活。
然而,我們後來發現,華人老闆每個捕魚季節付他們的薪水是 350 到 600 美元,而我們的薪水是 170 美元。
為什麼會這樣?
受工作束縛
我們和華人老闆的關係頂多比奴隸和主人的關係稍好一些。我們有六個月被經濟的枷鎖束縛在這份工作上,而我們很少人能夠切斷它。我們已經簽訂了整個魚季的工作契約。如果我們在此期間辭職,我們就會失去整個魚季的收入,除非中國佬願意發給我們。
但我們根本無法辭職。罐頭廠老闆擁有該地區所有的船隻,他們也掌控著僅有的無線電。
我們的罐頭工廠周圍是一片沼澤地,穿著高筒靴都很難穿越。靴子的價格是 8 到9 美元一雙。如果我們設法逃走,也只能逃到另一家罐頭廠,而所有罐頭廠都互相串通。他們不會僱用一個從另一家罐頭工廠辭職的人。
從華人幫逃亡的罐頭廠工人的唯一避難所就是印地安人的村落。然而,我已經察覺,即使是原住民也對華人幫抱著一種蔑視的態度。除非我們有足夠的現金可以回去——大約 150 美元——我們就必須硬撐下去,如果我們想吃飯,就必須工作。
華人被保護
然而,雖然我們在六個月內處於華人老闆的絕對權力之下,但魚季結束後他對我們就沒有興趣了。
但他對他的華工卻並非如此。年復一年,他為他們提供食物和住所。
有時他們全年住在他的住處並與在他那兒包伙。他們經常欠他鴉片和其他東西的債務。這種情況與已故的哈麗特·比徹·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所描述的情況如出一轍。
當「老闆」每個魚季付給他們 350 美元時,他不是付給他們,而是付給他自己。他們要麼已經欠他這個魚季的收入,要麼最終會在他那兒花掉。他把錢從一個口袋拿出來,放進另一個口袋裡,他付給他們的薪水越多,他自己賺得也越多。
這就是為什麼在華工契約制度下,罐頭廠永遠無法保證擁有一流工人的眾多原因之一。
下週預告: 第26篇 「 斯特恩在三名黑人的協助下組織了四重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