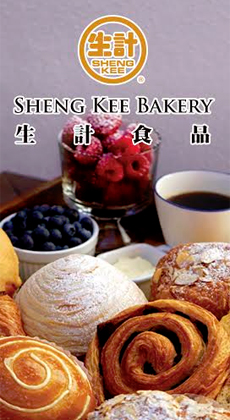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號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前書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花錢混入了” 華人幫” 團隊。工人們簽署了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三桅大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上船幾天後,大帆船終於從舊金山出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風暴來襲。每天僅能吃兩頓劣質食物,僅能有一杯水。高大魁梧的白人漁夫們在船上變成水手,斯特恩見識到他們的工作和個性,也認識了華人包商手下” 華人幫” 的烏合之眾。賭博、走私、剝削、疾病、危險、與死亡無時無刻地伴隨著這些人與” 地獄之船” 駛向遙遠的北方。
他們花了四週橫渡了 1600 英里寬闊的海洋,通過一個僅十英里寬的烏尼馬克海峽進入浪濤洶湧的白令海。終於,在古老的移民定居點努沙加克附近,他們拋下錨。
上篇摘要: 「TIERRA(陸地)!」 我們在海上的第四週即將結束,我們橫渡了 1600 英里寬闊的海洋,抵達了一個僅十英里寬的海口,它被稱為烏尼馬克海峽,由那座巨峰「摩西」及其兄弟「襤褸的傑克」(Raggedy Jack)把守。一天晚上,我們滑過「蘇格蘭帽角」(Scotch Cap)的燈塔,通過海峽進入浪濤洶湧的白令海。終於,在古老的移民定居點努沙加克 (Nushagak) 附近,我們拋下錨。我們花了 33 天完成了這趟旅程。
第23章 工人們住在低到無法站立的「房間」裡

圖解: 北美印地安人村。這些阿拉斯加原住民有一半愛斯基摩人血統,據說另一半是日本人,他們在布里斯托爾灣的每個罐頭廠附近都建立了自己的村莊。印地安勇士們經常在夏天在罐頭廠工作,在冬天設置陷阱和狩獵。 1918 年,許多村莊被「流感」完全摧毀,據說「流感」是由罐頭船隊的華人幫帶到阿拉斯加的。
我們在春天的翠綠燦爛中離開了加州,一個月後我們抵達阿拉斯加,卻發現這片土地仍沉睡在冬末的褐色外衣中。這已是六月的最後一周,但寒風依然從苔原上吹來,每條泥濘的河岸邊正在慢慢融化的積雪上都蒙著一層霜。
在我們的左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罐頭廠的輪廓,面向潮汐地。這是一個够淒涼的前景,我們卻渴望立即去到那裡。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被扣留在船上,直到幾乎所有的補給品都被運到岸上。於是,我們在「地獄之船」上又度過三天,無奈地等待命令。
父與子,九歲的夥伴
一名帶瑞典血緣的土著男人帶著他九歲的混血男童開著他的漁船向我們的船靠攏,他向廠長報名要求工作為公司捕魚。
1919年,罐頭船和白人將「西班牙流感」帶到阿拉斯加,他的妻子就是成千上萬的死去的土着之一。現在他和他的小男孩更是形影不離,每季都一起作伴出去捕魚。
隨後,幾個年輕的原住民勇士們駕著一艘汽艇登上我們的船,帶著各種各樣的紅狐狸皮來出售。這些皮毛是他們冬季捕獲的成果,售價為每張 9 美元。這個價格讓我們感到受寵若驚,因為我們全體都湊不出九塊美元的現金。
垂死的墨西哥老人
我們的船員幾乎都已恢復行動,除了一個人——那位年邁的墨西哥人,他已經是奄奄一息。
在大約五英里外的一個罐頭工廠裡有一間「醫院」,一名醫生會在捕魚季節駐紮在這裏。但這位醫生還沒從舊金山過來,所以墨西哥人躺在他黑暗的角落,無人照顧。
他甚至沒有得到赫克托的醫藥箱裡所能提供的護理。船長喬的斑紋小狗生病時得到了細心的照顧,但華人幫的一名成員卻不值一顧。
如果他被帶去看醫生,可能也沒有太大差別,因為阿拉斯加鮭魚漁場的醫療服務被每年來此工作的人視為一個殘酷的笑話。罐頭廠的醫生通常是年輕人或流浪漢,據工人們說,他們幾乎都屬於冷酷無情的一類。
無止境的等待讓我們心煩意亂。一天晚上在貨艙裏,這種焦躁終於在一場打架中爆發了。就像在雷克斯畢奇(Rex Beach)的電影中才能看到的那種場景。
這場打架是因一場紙牌遊戲而引起的。一名塊頭較大的關島男孩被一名年輕的哥倫比亞人指控作弊,這名年輕的哥倫比亞人是一個高個、膚色烏黑的蠻人,我們稱他為蠻達。
他們心中充滿殺機,互相撕扯著對方的喉嚨,周邊圍著一群黑壓壓搖晃的旁觀者。 他們在昏暗的船艙內描繪出一幅充滿了一種原始野性的畫面。
當蠻達伸手去拔刀時,眾人紛紛介入,好不容易費了極大力氣才把他們分開。幾天后,我們還擔心這場爭鬥會導致流血事件。
夜間出發
終於,在某個晚上,我們接到命令十點轉上駁船。我們不是在早潮時,反而在午夜時分被帶到上游的罐頭廠,這個決定在我們看來就是「存心折磨人」。
駁船裡裝滿了補給物資,上面舖著一塊大帆布。細雨飄飄,打濕了帆布,我們抱著捲毯坐在上面。雖然我們都上船時已經快十一點了,但在那日不落的地方,天依然亮著。
這位生病的墨西哥人並沒有被留在帆船上等醫生到來,或等到他能被轉送到「醫院 」,而是在夜雨和寒氣中與我們一起被遷移到岸上。
病人被留在雨中
很快,我們用兩根長槳和一塊帆布製成了一個擔架,墨西哥人被抬上駁船。放置在船上堆放的貨物中清理出的一小塊空間中。之後,我們中四個壯漢把他抬下了碼頭,那裡他就躺在寒冷的細雨中。
在五月阿拉斯加午夜的昏暗暮色中,一群瑟瑟發抖的華人幫終於從駁船上蹣跚地下了碼頭,那是堅實的陸地,這種感覺讓我們異常欣喜。
我們扛起自己的「包袱」,穿過一個長長的碼頭,到達一個在黑暗中勉強可辨認出來的宿舍。藉著燭光,我們各自選擇了住處。
無法站立在「房間」裡
即使在搖曳的燭光下,這間宿舍也可以讓眾神們大開眼界。這是一座又長又破舊不堪的玩意,兩側各有兩層舖位。這些舖位更像是狗窩。它們大約有八平方英尺,但屋頂卻低得讓人無法站直。
推開幾經修補的、掛在幾根皮條上的門才能進入,而上層的“舖位”則需踏著兩個隨便釘在一起的木箱爬上去。
我選了一個上層的「房間 」,爬了進去。裡面除了灰塵和一個木箱之外,什麼都沒有。我把蠟燭放在這一件「家具」上,我開始整理我的舖位。這裡沒有床舖,當然也沒有床墊或彈簧。
寒風穿牆而過
牆上有一塊木板缺失,吹進來的是一股河面上冰冷的風。它幾乎熄滅了我的蠟燭,所以我把衣服塞進洞口,我把凹凸不平的床墊舖在骯髒的地板上,然後鑽進被子裡。
屋頂是用木片,破鐵皮和鬆散的木板拼湊而成的,在這些屋頂和牆壁上有人用粉筆潦草地寫著「三藩市·法蘭克,世界產業工人工會 」。當我躺在那里瑟瑟發抖時,我開始理解我的前任和同名者的感受。
這是對我們所經歷的一切羞辱的無力的抗議,一個流浪漢的悲痛——正如愛爾蘭詩人、和小說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在《出深淵記》(“De Profundis) 書中所言。在這場徒勞的地下抗議擴展成震驚全國的反抗之前,我們還需要經歷多少像我們已遭受的待遇。
下週預告: 第24篇 「 宿舍屋脊成波狀;漲潮時,水淹沒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