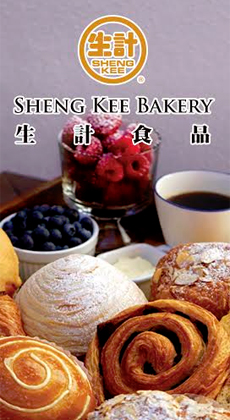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號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前書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花錢混入了” 華人幫” 團隊。工人們簽署了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三桅大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上船幾天後,大帆船終於從舊金山出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風暴來襲。每天僅能吃兩頓劣質食物,僅能有一杯水。高大魁梧的白人漁夫們在船上變成水手,斯特恩見識到他們的工作和個性,也認識了華人包商手下” 華人幫” 的烏合之眾。賭博、走私、剝削、疾病、危險、與死亡無時無刻地伴隨著這些人與” 地獄之船” 駛向遙遠的北方。
上篇摘要: 我們華人幫成員的配水量是每天一杯。奇怪的是,大家對伙食、跳蚤、劣質的衣服和被褥都有抱怨。但沒有可供洗滌的水是讓「華人幫」成員最煩惱的事。我交到了一位朋友——50 歲冰島人水手兼漁夫湯姆。我們常常長談海上生活及其危險。雖然水手或漁民的生活是艱難而危險的。但湯姆說「你可以怒吼,但你還是得去。」
第21章 在中國佬的貨艙中,矮子穿著睡衣大跳呼拉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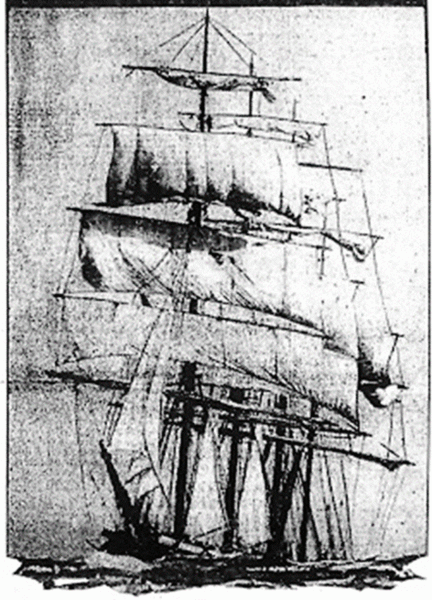
到了第三週的尾聲,我們再次進入無風區。三週內,我們經歷了兩度暴風雨和兩度風浪平靜。讓我們真正的體驗到了海上的生活。
太陽出來了,漁民也隨之出來。船舷兩邊,他們把魚鉤和魚線拋出,用鹹肉做餌。不久,幾條大鱈魚就在魚缐上掙扎著。
這是個非常適合釣魚的日子。十幾名漁夫整個上午都在忙著拖入一條條 30 多磅重的深海魚,然後將它們從船尾一路蹦蹦跳跳的順著滑溜溜的甲板被送進桑迪的廚房。不到中午,他們已經捕獲了超過 75 條。
華人幫也有鱈魚吃
一個義大利人拉上來一條巨大的、捲曲的魔鬼魚,其他義大利人抓住了它並把它切了做成一道別緻的菜。他們說,魔鬼魚的肉異常美味。
我們華人幫幾個成員自願幫忙清理它們,我們在冰冷的血水裡忙了好幾個小時。我們的回報是品嚐了桑迪以熟練之手烤製的一盤鱈魚,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令我感動的食物。
大多數沒有送到漁民餐桌上的魚都被意大利人醃在桶裡——留給他們自己,但二廚「餅乾」卻討到了幾條為我們在貨艙裡的人做了一餐。由於沒有烹飪設備,「餅乾」的鱈魚被燒焦了,淡而無味。我終於明白了「鱈魚貴族」這個名詞的含義。
摩西的運氣很差
在停滯了幾天后,風終於捕捉到了我們船上來回拍打的帆,讓我們迅速重新啟航。
我們的船艙裡依然籠罩著陰鬱的氣氛。除一名中國佬外,還有三名墨西哥人患病。病得最嚴重的墨西哥老人已經不再呻吟,整天整夜都處於昏迷狀態。對於摩西這個送水工來說,這看來是一筆好生意,他的副業是殯儀師,每場葬禮收費十美元。摩西有一年賺了 30 美元,但今年他的運氣很差。
跟著順風,雨和冰雹也隨之而來。有一天晚上甚至下起了雪,甲板太濕而且天氣冷得無法出去。
丟了褲子
我窩在舖位裡,藉著借來的一根蠟燭的燭光下閱讀《海狼》,我對比傑克·倫敦對縱帆船「幽靈號」的描述和我們油膩的帆船,感到非常有趣。我們的就是那樣的一個旅程,只差了浪漫。
一天早上,我的褲子不見了。我進行了一次靜悄悄的搜尋,發現它被藏在一個墨西哥人的舖位裡。他就是我懷疑偷我手錶和水的人。我報告了這次竊盜事件,班就搜尋了他的舖位。我們沒有找到手錶,但從那時起那傢伙總是瞄著我,彷彿隨時要用匕首捅我一刀。
一天晚上,有人建議開個舞會。於是我們從義大利漁夫那裡借了一把舊吉他,黑人鮑伯作了調音。一位神情憂鬱的雅基印地安人吹起口琴。
桌子和一些豬飼料已經從地板上狹小的空間裏清除,然後舞會就開始了。幾位漁夫應邀而來,籠罩著一種嚴肅的節日氣氛。
這無疑是我參加過的最奇特的「舞會」。 「胖子」,關島廚師,抱著他的伙伴,一個身材矮小的卡納卡人(Kanaka),他們在濕滑的地板上轉圈圈,不時地因船的晃動而撞到牆上。
穿睡衣,跳呼拉
兩個黑人舞蹈的方式足以震驚舊金山的紅燈區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漁民聯盟的隨行代表「矮子」用單腳和我們穿著大衣和高筒靴高大捲髮的墨西哥理髮師一起跳舞。最後,一個肥胖的墨西哥人,自誇為這批人中唯一穿了件睡衣的,走出來跳了一支草裙舞。他的動作充滿暗示和淫穢,但卻引來熱烈的掌聲,他不停地旋轉,直到渾身被汗水浸濕。
昏暗的人物在陰暗的貨艙裡有節奏地移動,在一盞老船上的燈和幾根蠟燭的微光下,讓人聯想到一幅叢林的畫面。
那場舞會顯得十分勉強,毫無歡樂可言。但這是華人幫唯一取樂的方式,而且作為「我們這類人物」在航行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社交活動,它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甚至有茶點
查理,這位總是考慮周到的華人廚師,抓住了節日的氣氛,在午夜時分端了茶點下來。他已經沒有絞肉和蘋果了,但他做了一些尚可入口的蛋糕,並配以熱茶。
「蛋糕啊!」他在角落裡喊道。 「十分錢。一大塊。」
我躺在床上,心情很低落。我因為處理鱈魚時著了涼,而舞會似乎把貨艙裡的氣溫加熱到了沸點。我願意抵押我獲得永生的機會來換取一小碟冰淇淋。
在中國佬艙中閱讀聖經
參加舞會的人們都回去了,但我下面燈下的箱子上坐著一個波利尼西亞人,口中哼著書上的東西。他的名字叫喬,是這艘船上最好的賭徒之一。他擁有我所見過的唯一真正的撲克臉,而且他在過去幾趟阿拉斯加之旅中贏了許多錢。他患有一種皮膚病,面色陰鬱。我問他在讀什麼。 他回答:「《聖經》。」
在我們的華人幫中,我處處看到墮落。我看到一個墨西哥男孩從地板上的垃圾中撿起大麻煙蒂,並將珍貴的大麻留下來製作新的大麻菸。
我看到另一個墨西哥男孩從白人的廚房偷偷拿了一根火腿骨,把它藏在枕頭下。
我甚至看到了退化的跡象。但最讓我驚訝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人們對知識的慾望、保持清潔的渴望、對美好事物的嚮往、無所不在的善意,這些東西和墮落的跡像一樣頻繁,使我們可以忍受這低賤的環境。在我們這樣的惡劣條件下,人們能夠渴望並奮鬥,這是整個航程中最有希望的事。
我躺着卻睡不着,我覺得自己開始發燒了。在我的旅途中,我第一次突然意識到沒有任何跳蚤在我身上爬行。
「天哪!」我想,想起了我的警衛朋友在家鄉碼頭上所說的話。 「我一定是病了。」
下週預告: 第22篇 「 經過 33 天的海上航行,到達鮭魚漁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