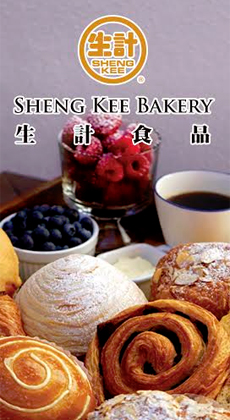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前書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花錢混入了” 華人幫” 團隊。工人們簽署了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三桅大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上船幾天後,大帆船終於從舊金山出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風暴來襲。每天僅能吃兩頓劣質食物,僅能有一杯水。高大魁梧的白人漁夫們在船上變成水手,斯特恩見識到他們的工作和個性,也認識了華人包商手下” 華人幫” 的烏合之眾。賭博、走私、剝削、疾病、危險、與死亡無時無刻地伴隨著這些人與” 地獄之船” 駛向遙遠的北方。
上篇摘要: 地獄之船终于解纜啓航。當我們偷偷地溜走時,沒有樂團演奏《Aloha》,也沒有揮動的手帕向這艘即將離開的船道別。拖船開始拖引,當我們越過法拉隆群島時,拖船鬆手返回。這艘三桅大帆船艱難地揚帆,她的鼻子指向夏威夷群島,她側着身逆風而行,前往遙遠的北方。
第13章 斯特恩發現阿拉斯加帆船上有 30 個國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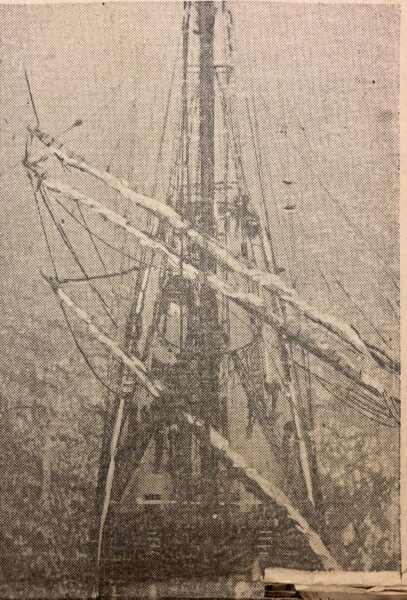
圖解: 斯特恩航行時所乘之船的難得的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在一個船塢拍攝的,展示了她的甲板上水手的視角。
出海的第二天,天氣驟變,寒冷又多風。這艘小帆船在猛烈的西北風的牙齒中緩慢地迂迴航行,幾乎沒有什麽進展。我們只能一次次地調整航向,逆風而行。
船長喬在後甲板上來回踱步,嘴裡咒罵著這該死的風。他穿著沉重的木底鞋,這像是他的同胞們在西部各州山坡上的乳牛場穿的一樣。他腋下夾著一隻有斑紋的小狗,牠是船上的吉祥物。
走動以保暖
我仍然感到有些暈船,需要些新鮮空氣,所以我把自己裹在紅色的毯子裡,瑟瑟發抖地站在在船艏的絞盤背風處。許多船員以兩人一組在中部甲板上來回快步走動,籍運動來驅散寒意。
這艘老船果真是一個大熔爐啊!桅杆上飄揚著星條旗,但在那面國旗下,我相信真正的美國人不超過十個。
我數了一下,船上至少有三十個不同國籍的人,甚至可能更多。有華人、關島人、尼加拉瓜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菲律賓人、夏威夷人、哥倫比亞人、巴拿馬人、多米尼加人、海地人、芬蘭人、俄羅斯人、拉脫維亞人、瑞典人、丹麥人、荷哇蘭人、德國人、挪威人、愛爾蘭人、黑人、冰島人、西西里人和英國人——全都融入了我們這支形形色色的鮭魚罐頭包裝公司的隊伍。
莫斯,一個身手矯健、面帶憂鬱表情的小夥子,正坐在前方豬圈旁,讓墨西哥理髮師給他剃頭。
海浪沖走了泡沫
理髮師和莫斯都有些醉意,而此刻的海浪很高。莫斯的頭皮上佈滿了血淋淋的傷痕,但他對周圍的人都調皮的咧嘴笑著。時不時地,一股大浪撲上甲板,將他頭上的泡沫沖洗得一乾二淨,但他和理髮師似乎都不以為意。
「這根本不算什麼,」莫斯咧嘴一笑,「你們應該試試在暴風雨裡繞過合恩角,每個新水手都得剃光頭,哇!天哪!」
莫斯原本是個水手,但被分配到了送水的工作。作為一名送水工,他完全履行了船長節約用水的命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還是船上的「葬儀師」,每當有人死去並被在他的指示下海葬時,他都能領取十美元的報酬。
曾經富有的黑人
是潮水把這麽一批雜亂的人從地球的四個角落沖刷出來並拋棄在我們的船上——其中不少人曾經見過更好的日子。
華人幫中有個名叫鮑勃的高個子黑人,他在某種程度上曾經小有財富,直到不幸之神趕上了他。他曾靠偷運華人苦力從墨西哥邊境到舊金山和奧克蘭賺了成千上萬的美元。
他如何在蒂華納(Tia Juana)將這些偷渡的亞洲人塞進他的凱迪拉克車廂底部,在夜色的掩護下瘋狂駕駛,白天則躲藏在洛杉磯和弗雷斯諾(Fresno)華埠休息,這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他在奧克蘭交付時每人頭能獲得1,000 美元,表現不俗,但後來他嘗試鴉片和烈酒作為副業,結果被捕並被罰——罰款相當於他的銀行帳戶和汽車的價值。現在他正試圖在賭桌上挽回損失。
前局長也在那裡
我們的另一位成員名叫馬蒂尼,是個膚色漆黑的小胖子,他曾是巴拿馬市的警察局長。如今,他虛弱得令人憐憫,終日躺在舖位上。
還有一位來自下加利福尼亞的前珍珠潛水員。他是個年輕俊美的生物,一雙黑色的眼睛閃爍著怒火,一邊低聲用奇怪的西班牙語詛咒梅耶和楊格的店鋪,一邊詛咒阿拉斯加的一切。
在漁民的前艙房裡,還有更多過氣的名人。
躺在床上,鼻子因醉酒打架而骨折,是一個拉脫維亞人(Lett),被稱呼為“男爵”。他曾是拉脫維亞擁有土地的貴族之一,但革命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現在和一群社會主義拉脫維亞人一起生活和工作,顯然已經忘記了過去的一切。
工作賺錢以上大學
船上的大副,也是拉脫維亞人,大家叫他「領事」。他曾擔任拉脫維亞駐某個歐洲城市的領事,如今四處漂泊,試圖賺些錢返回家鄉。
在海灘幫裡,有一個體格健壯的年輕愛爾蘭人,名叫派特。他走路的姿勢讓人確信他曾是個警察。他確實曾是舊金山的巡警,如今來阿拉斯加打工,希望能賺夠學費,以便上大學去讀電機工程。
「約伊」,夜班守望者,曾在荷蘭經營客棧。而他的朋友「布萊奇」,則是「猴子扳手幫」的鐵匠,曾經生意興隆,直到汽車產業把他和他的行業逼到了牆角。
厄運讓他們平等
諸如此類。很難把一群更奇怪的一群人聚集在同一艘船上,但他們都被最有效的民主化因素而削減成一種實質上的平等——那就是不幸的命運。
將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最大共同點就是厄運。
前甲板很快就變得太冷了,所以我在華人幫被允許活動的有限範圍裡走來走去。但不准我們超過中甲板的艙口。甲板上因沾滿了海水和泥土變得泥濘,我穿著價值 4 美元的鞋子沒走幾步,腳就濕透了。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我們的華人幫中有一個人對他的簽約感到高興。
出獄換來此行
事實上,我就像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 一樣,在尋找一個心滿意足的華人幫份子。
靠在豬圈邊,一個男孩望著海浪。他的國籍難以辨認,可能是葡萄牙人,但顯然是一個漂泊者。
「你覺得這趟旅行怎麼樣?」我問,「你開心嗎?」
「嗯……我想是吧,」他猶豫地說,「梅耶幫我在緩刑期間從監獄裡保釋出來,條件是要我承諾參加此行。我想,這可能比坐牢好一點……但我不知道。」
下週預告: 第14篇 “每人每天僅給一杯水用於飲用、洗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