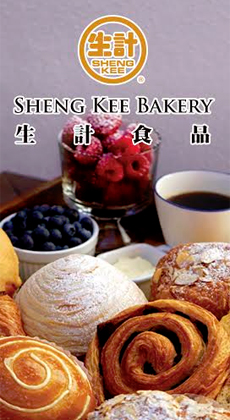作者:麥克斯·斯特恩(Max Stern) 1922
譯者:喬立(James Chiao), 喬成(Philip Chiao) 2025
《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號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第1 – 11篇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一方面華工減少,其他族群的工人不再服從華人包商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分包商的介入引發各種敝端。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工人們簽署了自己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 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混入了工人團隊,即所謂的華人幫。
上篇摘要: 斯特恩上了一艘老舊的三桅木製大帆船。走下到擁擠的“華工貨艙” ,裡面又黑又髒,也沒有任何通風設備。每個人都從四排舖位中挑選自己的床位。他簽了一份他沒有看見的契約,拿到十塊錢,然後就被迫留在船上。
第6章「華人幫」向海鷗丟去吃不下口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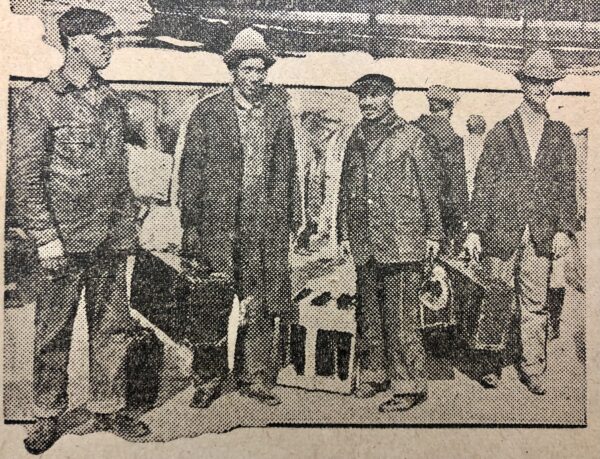
圖解: 一些乘坐三桅大帆船出行的男人
兩名守衛在碼頭上來回巡邏。
他們是阿拉斯加鮭魚罐頭商僱用的私人警衛,負責在船隻出發前看守船支。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確保沒有華人幫的成員偷偷逃離上岸。
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想上岸。我走回船頭我們的住處時,我看到一個小個子的卡納卡人(波利尼西亞人)正懇求班允許他上岸。
他還很年輕,剛剛結婚。他的家就在電報山東坡,離我們的停泊點近得幾乎只有一石之遙。
被拒絕,他哭了
想到自己要在以後三天裡與新婚妻子近在咫尺,卻無法見她,這讓他無法忍受。
當班給了他和我相同的回答時,這個年輕的卡納卡人走到船邊,把頭埋進手臂裡,像個孩子般哭泣起來。
我望向東方,已是黃昏時分,像薰衣草紫色的霞光開始柔和地勾勒出海灣對面十英里外的皮埃蒙特山丘(Piedmont Hills)的輪廓。柏克萊的大學城籠罩在一片淡藍色的薄霧中,白色方尖的鐘樓高高聳立,穿透霧氣。這裡是我的居住的城市,我過往熟悉的一切都似乎近在眼前。
晚餐時間
穿過平靜傍晚的水面,我聽到大學的鐘聲敲響了四點鐘。綠草如茵的校園即將湧入穿著運動服出來鍛鍊的男生,以及下課回家路上的漂亮少女。
就在這時,我聽見身後有人敲打錫鍋的聲音。
我轉身一看,發現已經是晚餐時間了。
我的華人幫的同伴們正擠在船頭的廚房周圍。那是一間搭建在甲板上的小棚屋,看起來非常簡陋。它被一條鋼纜綁住,以防被浪沖走。
我們所有食物都在廚房那準備,這個廚房的入口距離廁所不會超過三尺。而十尺之外則是一間有頂棚的豬圈,裡面傳來飢餓的豬叫聲。溫暖的甲板上已經瀰漫著一股惡臭。
燉肉當晚餐
廚房門口站著胖胖的關島籍二廚。他正分發一組平底錫鍋,每個錫鍋約一寸半深,在整個旅程中給我們當盤子使用。我們還每人得到一個錫杯。很快二廚就被大家取了個綽號——“胖子” ,胖子開始分發我們的晚餐。
他從一個大錫盤裡倒出了燉肉。接著,他用一把大湯勺從一個洗衣盆裡舀出一種棕色的溫熱液體,他稱之為咖啡。第三個桶則裝著一片片厚達兩英寸的乾麵包塊。
我們端著食物來到船舷的欄桿邊,站在那裡試圖去吃它。
燉肉裡只有三種食材——馬鈴薯、肉塊和肉汁。
用手指吃飯
我們沒有被分配到刀叉或湯匙。只好回歸到最原始的武器,用手抓著燉肉吃。馬鈴薯雖然佈滿黑點,至少還能入口。但那肉卻是個問題——那是我牙齒爭戰過最堅硬的肉。經過幾次徒勞無功地嘗試後,我放棄了,把它扔出船外給了海鷗。
沒有奶油可抹在乾麵包上,我只好將麵包沾著已經冷掉的肉汁勉強吃下了半塊。接著,我嘗試喝那飲料。
啊,咖啡,人們以你的名號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
這混合物具有我所認知的咖啡的三種特性——它是棕色的,它是溫熱的,它是甜的。但它的味道卻與我嚐試過的的咖啡完全不同。它顯然是用某種烤焦的穀物沖泡的,再加了一點罐裝奶和糖。我幾乎無法下嚥,然而這將是我們整個季節唯一的飲料。
我用這種叫做“咖啡” 的溫熱液體沖洗了錫盤,用剩下的麵包皮擦乾它,然後把盤子和杯子塞進我船艙的舖位裡。晚餐結束了,我卻依然飢餓,但再也吃不下更多那種施捨給我的食物了。
包裹送達
大約五點,我們的包裹開始從梅爾與楊格恩的商店運到了。一名男子開著一輛貨車駛入碼頭並把包裹堆在碼頭邊。在他叫出號碼時,我們身體半懸在船舷邊等待。每當我們中的一人聽到自己的號碼而舉手時,司機就將包裹從船舷下扔上來給他,他接住後就帶到下面去。這「幫」人中沒有人看過他買的東西,這帶來了一種奇特的興奮感。就像就像自己小時候一樣,到了教堂的聖誕樹下,並收到聖誕老人送給我們的驚喜禮物。
終於我得到了我的包袱,帶下艙後放在舖位上。但我無法忍受船艙中那污濁的空氣,於是決定等到晚上再打開它,然後再次回到甲板上。
我倚靠在船舷靠岸的一邊,引起了碼頭上一名正在抽煙的守衛的注意。他似乎對我出現在華人幫裡感到有點驚訝,於是問我的名字和上船的原因。我便向他重複了有關我眼疾的說詞。
與守衛友好
(“哦……”他聽了大笑起來……“那鮭魚……。”)
我們漸漸熟絡起來。我鼓起勇氣問他,是否介意我陪著他在碼頭上來回走動。他覺得應該沒問題,只要我不在船下待太久的話。
我從船舷爬下,順著一條繩索溜到地面。慶幸自己能離開這艘又髒又臭的船甲板,竟管只有一會兒。
當我走進碼頭的黑暗盡頭時,我遭遇了這趟詭異旅程中最離奇的經歷之一。如果有什麼能讓我打消出航的念頭,那就是我在短暫的「上岸許可」下來的這幾分鐘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
下週預告: 第7篇 “阿拉斯加「地獄之船」上的三種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