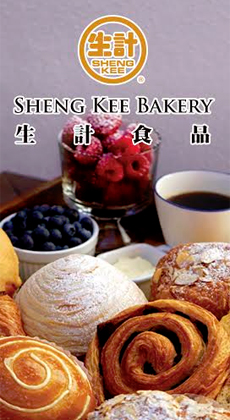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鮭魚何價》(The Price of Salmon) 最初由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於1922年在《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連載發表,共計37篇文章。
斯特恩自1920年起擔任《每日新聞》記者及政治評論家,並因揭露「阿拉斯加鮭魚罐頭產業在西海岸的醜聞」而聲名大噪,當時此系列報導曾引發相當程度的轟動。2022年由喬立與喬成兄弟編輯成書以英文出版。今年更以中文發表以嚮廣大的中文讀者。全書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已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老中網上登出,其餘三十五篇於四月十九日開始,每週六連載,敬請讀者関注。
第1 – 11篇摘要: 華人曾經多年把持美國西部鮭魚罐頭工業的低階勞工市塲,但在1920年代,大部分華工已被其他族群取代。華人包商仍然活躍,但盛極一時的華工契約制度已經腐敗。一方面華工減少,其他族群的工人不再服從華人包商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分包商的介入引發各種敝端。華人包商透過一個分包商來招聘工人,而這個分包商向工人推銷裝備以獲暴利。工人們簽署了自己從未見過的契約,隨後被塞進老舊、臭氣熏天的大帆船貨艙裡,這些帆船組成了阿拉斯加罐頭公司的鮭魚船隊。由於船上環境極端惡劣,這些大帆船被稱為”地獄之船”。 斯特恩被《舊金山每日新聞》派去調查真相。他化裝成流浪漢混入了工人團隊,即所謂的華人幫。
上篇摘要: 工人必須透過分包商訂購裝備來買工作。舊金山《每日新聞》(San Francisco Daily News) 派記者馬克斯·斯特恩 (Max Stern) 偽裝成個流浪漢,去舊金山華埠和北海灘區之間的一家商店尋找阿拉斯加鮭魚產業工作的機會,這家店就是邁耶和楊格(Meyer & Young)。
第三章 記者與舊金山公司報名去阿拉斯加為華人老闆工作

圖解: 這些老舊的船隻在秋季被拖往舊金山灣的某處停泊過冬,春季則被拉出來前往阿拉斯加鮭魚漁場。這些古老的船隻,除了這項用途,已無其他價值。左下角:馬克斯·斯特恩(Max Stern)登上碼頭時的照片。
那個瘦小糟老頭給了我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往阿拉斯加鮭魚工作的門。這與打開美國社會中許多機會之門是同樣的鑰匙——一把銀色的鑰匙。
但梅耶曾經拒絕過我一次,我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插入這把鑰匙。我需要的是一個「門把」。
當我再次沿著霍華德街走時,我經過了幾個一人當家的小型職業介紹所,這些店家因缺乏備案的工作,幾乎無人問津。突然間,我心血來潮,決定走進其中一家。
「我想去阿拉斯加。」我對從後方走出來的一個肥胖、穿著過份正式的男子說。
他告訴我可以試試阿拉斯加包裝商協會(Alaska Packers’ Association)。
「我已經試過了,但沒有找到工作。」我回答。
「如果他們肯僱用一名白人,我願意加入華人幫。」我說。「我有一點錢,如果有人能幫助我報名,我很願意花錢買一套裝備。」
我把口袋裡的幾塊錢幣搖晃的叮噹作響。
「門把」成本 2 美元
「我看看我能做些什麼。」他爽快地說,隨後退到後面,拿起電話。
我聽到他打給華埠的楊格(Young),說有位朋友想去阿拉斯加。接著,他壓低了聲音,我聽不清後面的對話。
不久,他拿著一張寫給楊格的字條走了出來,遞給我,並示意我去找楊格。他向我收了 2 美元,說這是「提供正確求職資訊」的費用。
我的介紹人是 米契爾 公司 (Mitchell & Co.) 的R. S. 米切爾。
我有了我的門把。這筆交易只花了 2 美元,卻出奇地有效。
我重新穿過市場街,來到華埠。在商店裡,我把字條交給楊格。它就像魔法一般——楊格向站在玻璃櫥窗後、像木雕印第安人般一動不動的墨西哥胖子點了點頭。
用訂單「報名」
「去那邊報名吧。」他說。
「報名」該是一個冗長的過程。。我以為他們會記錄我的姓名、地址,甚至某些家庭成員的聯絡方式。但是墨西哥人卻撈出一張藍色的訂單放在我面前。
他只記錄了我的名字,一個假名。我本以為需要提供住址,還特意去租了一間房間,但這完全是不必要的預防措施。整趟旅程中,沒有人問過我住在哪裡,也沒有人詢問在我生病或死亡時應該通知什麼親友。
不過,我被分配了一個號碼。整個鮭魚捕撈季,我都像囚犯一樣,背著這個編號。我是514號。
當我正在訂購裝備時,梅耶(Meyer)走了進來。他帶著懷疑的眼神打量著我,然後在楊格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但楊格向他保證:「他是米切爾先生的朋友,一切沒問題。」
我記得那個白人小糟老頭曾告訴我要多花點錢購買裝備,但我手頭只有幾塊錢,於是我建議稍後再回來採購。
信用良好
那名墨西哥人向我保證裝備的費用會直接從我的薪水中扣除,我現在不需要現金。
這張紙是一張印刷好的帳單,抬頭寫著公司的名字:「S.楊格裁縫公司、阿拉斯加裝備商、男士服裝部」。
價格看起來相當昂貴,但我想這些裝備應該品質極佳。我要去的是氣候嚴酷的阿拉斯加,加上旅途寒冷,我需要最厚實、最保暖的衣物和被褥,即使價格高一些也值得。
我問墨西哥人東西在哪裡。我想在購買之前先看看它們。
購買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會直接送到船上,這裡沒有任何現成的貨品。」他向我保證。我必須就此感到滿足。
我的帳單總額為 62.75 美元。對於一份最多只能賺 170 美元的暑期工作來說,這筆費用相當龐大,但我確實需要我訂購的所有物品,甚至更多。雖然我已經有了許多楊格清單上的東西,但如果我是一個真正潦落的遊民,我該需要更多的物品來確保自己的舒適。後來我才知道,我的帳單其實並不算特別高。大多數人花費在 20 到 60 美元之間,甚至有些高達 100 美元。
在楊格裁縫店的樓上,我量身訂做了一條燈芯絨褲子,他說會盡力趕製,並為此向我收取14 美元。
我使用的新名字是弗蘭克·斯坦納特(Frank Steinert),但邁耶和楊格公司已將我當作一個墨西哥人報名,以方便我過關。
換句話說,我實際上是透過賄賂分包商,以墨西哥人的身份被雇用,並且獲得了在阿拉斯加夏季工作的保證。
為中國佬工作
但我並不是為阿拉斯加包裝商協會工作,也不是為「飢餓的」彼得森(”Hungry” Petersen)、阿拉斯加鮭魚公司(Alaska Salmon Co.)或任何正式註冊的鮭魚罐頭公司工作。我也不是為梅耶與楊格工作。
我受雇於一名神秘且富有的華人老闆。
我不認識我的老闆。在整趟旅程中,我從未聽說過他的名字,甚至直到幾天後,我才知道我的老闆是一名未知的東方人。然而我,一個白人,一個美國人,竟然直接受雇於一個生活標準與社會理念與我們截然不同,有如日夜之差,的種族。
我現在身處於最奇怪、最不美國化,卻存活下來嘲笑我們民主的一個機構 — 這就是阿拉斯加漁業的華工契約制度。
在加州淘金熱時期,砂金礦營地的廉價勞力幾乎全由華人苦力提供。當1870 年代,第一批鮭魚罐頭廠在薩克拉門托河(Sacramento River)建立時,由於沒有其他工人願意做這類工作,因此很自然的由華工承擔。白人業主們發現華人「清客(chink)」不僅是優秀的漁夫,還是勤奮的工人。儘管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的詩歌《誠實的詹姆士》(Truthful James)曾諷刺「華人廉價勞工」,但「華人廉價勞工」並沒有毀掉那個年代的白人。
隨著鮭魚罐頭廠在薩克拉門托河地區的擴張,魚量很快枯竭,於是產業轉移至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與普吉特灣(Puget Sound),然後又進一步推進到阿拉斯加。
最早的黃金漁場位於阿拉斯加東南部,然後擴展到阿拉斯加中部,如今則是在布里斯托爾灣(Bristol Bay)與其支流,這裡有數以百萬條的鮭魚資源。在每個罐頭廠先驅者的遷移發展中,華工都在罐頭廠裡做沒有人願意做的苦工和雜活。後來他們變得專業化,同樣的苦力年復一年地進入罐頭船隊的船艙。我遇到了一位中國佬,他已經連續 30 年每年都前往阿拉斯加。
使用的契約制度
華人是精明的商人,但同時也是可靠的合作夥伴。白人業主發現,讓華人老闆來負責招聘苦力,比自己招聘來得更容易。於是,他們建立了所謂的華工契約制度,其運作方式大致如下:某個阿拉斯加罐頭廠的廠長——比方說史密斯先生——在春季初會向市場釋出訊息,表示需要招募廉價工人。這時,王和、海星和雷祖)等專門承攬華工的華人老闆,便會離開他們在華埠的豪宅,前往這廠長的辦公室洽談。
假設史密斯先生需要工人來處理 45,000 箱鮭魚,這些東方人便會出價競標。雷祖願意以每箱 35 美分作這項工作。他的出價最低,他得到了合同。從這一刻起,所有的雇工責任與煩惱都落在這位華人老闆的肩上。他不僅要負責招聘工人,還要提供膳食與支付工資。而罐頭廠的廠長唯一的責任就是提供這些工人住宿空間——通常是在船頭的貨艙及罐頭廠的宿舍。
勞資雙方沒有簽署的協議,華人老闆的一句話就足夠了。
只要「華人老闆」的勞工僅限於華工,這套制度的運作還算令人滿意。這些苦力吃得很少,只需要大量的茶、米飯、少許魚和海藻,就能維持體能保持正常運作。至少,他們不會發動罷工。
然後苦力被禁止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苦力勞工狀況逐漸成為加州的社會問題,最終促使國會通過《排華法案》。隨著華人苦力的數量減少,罐頭廠不得不尋找其他勞工來填補。黑人、白人、菲律賓人,最後還有墨西哥人,被陸續引進來取代年老和垂死的華工。然而,隨著新罐頭廠每年不斷地湧出,黃色勞工的供應開始迅速萎縮,然而華工契約制度卻繼續存在。
罐頭廠曾試圖雇用日本人,但發現日本工人與華人工頭及華工完全無法相處。在舊金山,日本勞工已多年未被雇用。然而,在普吉特灣與阿拉斯加東南部,有些罐頭廠的勞工團隊完全由日本人組成,這些工人則由日本工頭負責管理。
1920年的數據顯示了華工的減少。1920 年,阿拉斯加漁業共雇用了 27,482 名工人,其中有: 16,052 是白人,3783 當地人; 2369 華人; 1445 日本人; 1587 菲律賓人;1679 墨西哥人; 307 名黑人和 310 名其他各地來的的工人。
現在有更多的墨西哥人
在近年來鮭魚產業最新的發展地區,阿拉斯加西部或布里斯托爾灣,墨西哥工人的數量達到 1227 人,而華工則為 691 人。今年,墨西哥工人與華工的比例甚至接近三比一。
然而,新來的工人並不如舊一代工人那樣適應華人老闆的管理方式。西方工人不習慣吃米飯、茶和海藻。每年,「肚子罷工(belly strikes)」與叛變事件時常發生,導致整個阿拉斯加航程變得很不安寧。有一年,美國聯邦警官甚至不得不介入,命令華人工頭提供適當的食物,否則就要召來稅務巡邏船,將這些不滿的工人遣返回舊金山的家中。
導致這種不滿的不僅僅是食物。對美國工人而言,由華人老闆雇用、為華人老闆工作,這種想法讓他們無法接受。
華人使用詭計
然而,華人老闆並沒有放棄這種制度,而是採取了一個詭計。雷祖將招聘勞工的業務轉交給一名白人分包商,而自己則退居到昏暗的幕後。
於是,就有了梅耶與楊格(Meyer & Young)這公司。
華人包商在鮭魚產業中已經賺取並仍然賺取著成千上萬美元的利潤。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百萬富翁,開著豪華轎車出入華埠。在西雅圖,華人領事官阮洽(Goon Dip)也是阿拉斯加的勞工包商。這些華人老闆在他們移居的土地上養肥了自己。然而,他們的工作純粹是一種寄生蟲的性質,他們的致富之路則鋪滿了工人的痛苦、貧困,甚至死亡。
我如今深信鮭魚產業的這種勞工契約制度,對美國勞工理念的破壞,比以往任何步驟更具有破壞性。
第二天,我就會親身見證在工人與資方之間,在第二個中間人被引入後,會給這些鮭魚工人的負擔上增加多少新的痛苦。
下週六預告: 第4篇 “每年春天,老舊的帆船組隊向北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