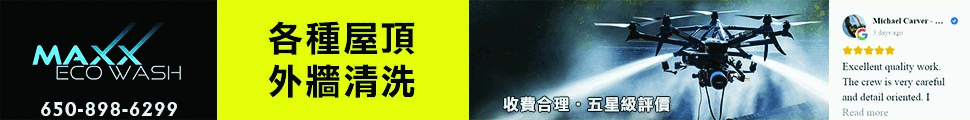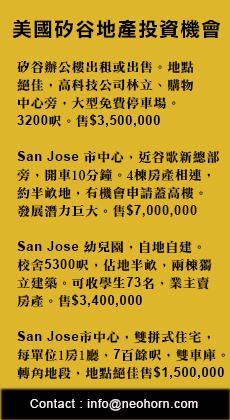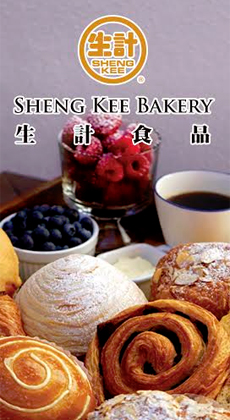何雷蒙(Raymond Ho,音譯)2012年入讀大學,當時他滿腦子都是新想法和對新生活的憧憬。開學第一個禮拜,他遇到一個同樣來自聖荷西的同學,「他想問的問題都和我一樣」。
這兩個人很快就成了好友,當了三年室友,他們經常交換各種想法和意見,從政治聊到個人生活,情誼變得愈來愈深厚。
何回憶:「我們總是聊得很開心,雖然他的觀點明顯比較保守,但我尊重他的看法。」
直到2016年。
當總統大選白熱化時,何表示,他的朋友(基於個人隱私何不希望公開其姓名)開始呼應一些川普競選活動中出現的極端言論,一開始是批評無證移民或女性,逐漸,兩人之間的火藥味愈來愈濃,意見愈來愈分歧。
何說:「有時候,我們之間的對話完全沒有邏輯基礎可言,純粹是價值觀上的衝突,最後總是不歡而散。」
何最後順利畢業,他的朋友因為罹患憂鬱症和焦慮症休學,成為一名焊接工人,經常向何抱怨「上天對他不公平」。
何的朋友和其他數百萬名美國人一樣,透過川普找到發洩的出口。儘管兩人在政治理念上的日趨分歧,關係有些緊張,但並未完全決裂,他們偶爾還是會見面。
在夏洛茲維爾發生流血事件後,一切都改變了。
何說:「夏洛茲維爾事件後,朋友在臉書上傳了一張照片,上面是他的白色馬球衫和卡其褲,旁邊附註『抱歉了』。」這套衣服在新納粹主義者與反示威者8月的衝突事件發生後,在社群媒體上爆紅,許多新納粹主義者都穿著相同的服飾。
何認為,朋友的舉動就算不是一種認同,也代表了他同情白人國家主義者。
當世界天翻地覆
觀看種族衝突照片時,我們很容易忘記,最深的分歧通常存在於親密的人之間,而非陌路人之間,這樣的經歷將使受影響的人改變對所有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的看法。
從小到大,何雷蒙一直認為多元化的聖荷西和矽谷是大都會性的、成熟的、舒適的地區,和自己一樣,但此刻他不再確定。
「人們會覺得這種種族敵意離我們很遙遠,」何雷蒙說:「但是,我看到它發生在我眼前。」
今年稍早,他和數名友人站在聖荷西周邊一個富裕的郊區金寶市(Campbell)一家酒吧外,他是這群朋友中唯一的亞裔。他說,一名自稱是當地官員女兒的白人女子主動上前對他挑釁,口出種族侮辱字眼,並說他不屬於這裡。
他回想:「她罵我是小亞洲佬,取笑我的眼睛,還叫我滾回我原來的地方。」
他當時因震驚過度不知如何回應,他的朋友們沒有一個為他挺身而出。
當晚,他說:「我開始覺得當一個亞裔很丟臉。」
在這之前,何從來不覺得他的族裔身份足以將自己與他人分割,甚至覺得自己「太美國化不像華裔」,不太能融入矽谷的華裔移民社區。
而現在,他懷疑自己是否「太華裔不像美國人」。
他最近的經歷也讓他對身邊的人產生疑問,不論是陌生人或朋友。他說:「有一天我坐在一家速食店內,我開始好奇,坐在我身邊的人到底是怎麼看我的?」
尋找答案
這個效應也波及了他的家人。
何的母親琴經營一家中文新聞媒體,對象是聖荷西市與周圍地區的華裔移民社區。琴表示,兒子遭遇這些事後出現憂鬱症狀,因為他覺得自己被這個社會排擠。
她在一封電郵中寫道:「我心虛地告訴他,他在酒吧遇到的人,和那些夏洛茲維爾的人,並不代表美國大部分的民眾。我的兒子聳聳肩出了門。我真希望我能給他一個答案。」
她補充,她對她周遭的人的「信心」和「信任」也開始瓦解。最近,採訪完本地一場記者會後,電梯裡站在她身旁的一名男子瞄了她的名牌,以一種她無法解讀的口氣問她:「所以,妳是中文媒體?」
她回憶,她不知道這名男子是在嘲笑她的華裔身份,還是只是友善的招呼。「當時我的腦中湧出無數種情緒,不安、懷疑,最明顯的是 — 害怕。」
她還說:「我在美國已經住了38年,從來不曾有這種感覺。」
何雷蒙和母親一樣,正在為了將他周圍形成的新現實合理化尋找答案。他最近與人合夥準備在薩拉度加(Saratoga)開一家麵店,不過,他也想過發展其他事業,包括從父母家鄉台灣引進一個融合美國時尚的傳統服飾品牌。
「有人想劃清界線,玩分裂的遊戲。」他說:「我希望做出能展現所有元素於一身的服飾。」
本報導是由新美國傳媒與ProPublica「記錄仇恨項目」合作製作。舉報仇恨犯罪,請填寫此份表格。所有報導在歸入一個全國資料庫之前會先進行驗證,這個有隱私限制的資料庫將來會提供給美國各大媒體和人權組織使用。舉報表格不會提交給執法單位或任何政府機關。
圖文/New America Media Peter Schurmann